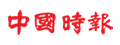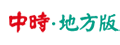愈絕望 愈不能喪失愛的能力
《如此歲月,如此幸福》懷著那份對世界的愛 儘管同時感知現實的殘忍 我仍說出心底的詞
-164514.jpg)
還記得二○一五年那個叫Aylan Kurdi的三歲男孩嗎?他躺在土耳其沙灘的畫面,如天使般的臉龐,短暫融化了人類的冷漠。那個姿勢如夢見未來生活的美好;天使不要再逃,不要再看見人類的殘酷,他以一己之死,在又暗又黑的水旁,敲打了我們古老心底的善良。
但人在某種的情境中,會喪失哭的能力;喪失同情的能力;喪失愛的能力;喪失憤怒不平的能力。
包括記憶的能力。
我們選擇性的「失憶」,因為我們如此自私,我們拿亂世沒有辦法,我們一方面稱自己渺小,無能為力;一方面卻又把自己的情緒、名利、奢望、利益無限擴大。
Aylan Kurdi剛死的那一天,他的軀體躺在一波又一波的海浪旁,四下沉默,只有浪聲,沉默的天地突然成了一種呼喚,呼喚每個人人性中僅存的良知……
於是,現在回想起來如天方夜譚,英國大批民眾上街頭抗爭保守黨及工黨政客自私拒絕收留難民;奧地利兩萬人發出怒吼;拒絕Kurdi家人簽證的加拿大政府大樓外,人民咆哮……
那一天,世界的「人道燈火」,因為Aylan的死亡不再熄滅。
但僅只一天。
如今「敘利亞難民」如一個外太空名詞,他們不在美國總統候選人嘴裡,包括賀錦麗;不在歐盟的議程文字裡,包括馬克宏。他們只出現於以黎戰爭,從黎巴嫩再度逃亡的難民潮中。
或許Aylan Kurdi是上帝派來世間最後的使者,考驗這個世界值不值得上帝眷顧。
或許神曲畫下了句點。所以從此以後,我們看到的殘酷故事,戰火紛飛,漸成日常。
殘酷又絕望的世紀,你還會憤怒嗎?還是逃避?自己過好日子享樂?
我會憤怒。我沒有能力參與無國界醫生組織,或是世界戰地的救援組織;我的身體病了,但我的心,沒有生病。它還在跳,還會生氣。
二○二四年十月二十日深夜,我看到紐約時報一則非主新聞的報導:〈全世界看著他被燒死〉。
故事是一名十九歲的加薩男孩,他是母親誇耀的兒子:小時候已背下整本《可蘭經》,並在大學醫學院名列前茅。加薩戰爭打斷了他的人生夢想,他想成為一名醫生。但當下最重要的是,這位名叫沙班.達盧(Shaaban al-Dalou)的男孩得先逃跑。逃離加薩。
自從以色列一年多前對哈瑪斯發動毀滅性報復攻擊以來,十九歲的達盧在社群媒體發表熱情洋溢的呼籲,公開了他逃難的「家」:一個小塑料帳篷,他沒有向命運投降,在GoFundMe的網站上設了一個頁面,呼籲看到這個頁面的人們,為他們全家的逃亡提供協助。
但命運和他想像的相反,全世界最終看著他被活活燒死。
十九歲的達盧被家人認出,他就是以色列火燒加薩走廊中部醫院一部駭人的影片的人物,那裡正有一個被火焰吞沒的年輕人,他無助地揮舞著雙臂,試圖掙扎,並且高聲朗誦經文。
當時的他不敢相信,命運會如此不偏不倚,如此不饒不恕。
這個影片,日後將成為加薩平民遭以色列無情殺害的象徵。它比當年納粹的「安妮日記」、越戰身上著火光身子逃跑的女孩照片,還令人震撼。
類似達盧的巴勒斯坦人,他們心中也都心裡有數,等待死亡,無論身懷什麼夢想。
他們沒有未來,未來是揮舞的火焰,直到死亡的疼痛吞噬之前。
達盧死的那一天是二○二四年十月十四日。請好好記住。
當天,以色列對加薩中部沿海城市代爾巴拉赫「阿克薩烈士醫院」附近轟炸,以色列號稱他們正對附近的哈瑪斯指揮中心進行「AI精準打擊」。他們的「精準」打擊,卻打到烈士醫院,包括醫院內旁邊的停車場。達盧一家人正住在這裡。他們早已被迫逃離北加薩家園,他們和十多個家庭,在醫院院內停車場,搭起了帳篷,當成臨時的家。
他們曾希望聯合國禁止以色列針對醫療機構攻擊,他們曾希望國際法能夠確保醫護及無關哈瑪斯的巴勒斯坦平民安全。但是在美國護航下,以色列已經不需要遵守戰爭法、國際法,而且不允許被譴責。
以色列軍方表示,吞沒達盧之家爆發的火災,很可能是由「二次爆炸」引起的;但《紐時》表示:以色列軍方說不清楚二次爆炸到底是什麼意思。
影片第一時間由Middle East Eyes公布,以色列國防部馬上表示:它是假的、被捏造的。但經過法國France24、英國《泰唔士報》、英國Sky News紛紛證實其為真,說謊的是以色列軍方。《紐時》再經由查核部門及AI確認軟體,也證實是以色列的無情戰火活活燒死了達盧。
美國紐約時報公布真相後,以色列官方又加了一個補充說明,「目前事件正在接受審查中」。典型官方說法。
以色列政府非常有把握會有下一個死亡,或是大規模的戰爭,足以讓我們遺忘此事,遺忘達盧的名字。他們充分知道,我們既是自私鬼,也是「失憶人」。
當大火燒毀達盧家族的帳篷時,父親艾哈邁德先跑回了屋裡,他帶著年幼兒子和兩個大女兒,逃到安全的地方。
當他回頭時,他的大兒子已經身陷火海。「我可以看到他坐在那裡,舉起手指祈禱。」
他正念著一種在出生和死亡時,穆斯林背誦的信仰信條。「我對他喊道:『沙班,原諒我,兒子!對不起!我無能為力。』」
沙班.達盧,在二十歲生日的前一天去世。他去世那一刻,不僅銘刻於父親的記憶中,影片也傳遍聯合國。
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格林菲爾德表示,她「驚恐地看到影片湧入我的螢幕。」
這位數次代表美國於安理會投下否決權,在聯合國大會投下反對票支持以色列的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終於說了她忍住許久的真話。她代表美國發出一封遲來近一年的聲明,交給聯合國祕書處:「沒有任何言語,根本沒有藉口,可以描述我們所看到的一切。」
「以色列有責任盡一切可能,避免平民傷亡,即使哈瑪斯在醫院附近活動。」
達盧一直是個信仰上帝,相信善良的好孩子。他曾在帳篷中開導其他人,「你要相信你自己和你的感覺」、「我們不會參加恐怖行動,它救不了巴勒斯坦人,繼續努力下去,上帝會為我們的族人開出另外一條路。」
達盧在死前,曾透過社群媒體尋求逃亡的金錢援助:「請你們為我們敞開心扉。我十九歲了,我不要在這無望的戰爭埋葬我的夢想。」在Instagram上一篇貼文中,他寫道: 「請支持我,讓我有機會找到我的夢想。」他的募款活動籌集超過兩萬美元。捐款者包括海外阿拉伯人,還有一些歐洲人、美國人。這筆錢其實足以支付高昂的逃亡費用,包括他和他的親戚逃離加薩。但一切的努力,最終徒勞無用。
因為二○二四年五月以後,以色列關閉了通往埃及唯一的拉法過境點,包括費城走廊。這個行動,困住了所有加薩居民,使得任何逃亡變得不可能。
以色列的理由是:他們不希望哈瑪斯逃出邊界,之後又死灰復燃。
埃及同意的理由是:他們接收不了兩百萬巴勒斯坦難民。
聯合國救援組織數次想突破此封鎖,包括一個叫「中央廚房」的救援機構。由西班牙的一位主廚發起,總部位於美國,一群廚師們響應,他們在烏克蘭、加薩傳送食物。他們進入拉法前已通報以色列,卻連遭兩次以色列軍隊砲轟,損失兩台車輛,死亡七名國際志工。
以色列的理由:「溝通不良,誤炸」。加上逗點剛好七個字,搪塞七條歐美偉大志工的命。
被火活活燒死的達盧姑姑向《泰晤士報》展示五月份,達盧一封短信問她,「他反覆發作的罕病,是否可能使他依國際人道法,具資格接受醫療送至埃及?」她回答說,這不太可能,即使是她的一個朋友,「妹妹失去了一隻眼睛,也找不到讓她出去的方法。」
但達盧仍相信上帝,常和她在帳篷裡吃午餐的侄子,似乎相信世界仍有公理,鎮定自若。他會看新聞,分析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及美國總統拜登的講話,然後告訴她:「戰爭會結束的,正如從前一樣。」「樂觀一點,一切都會好起來的。上帝保佑,上帝會幫助我們的。」
火焰中,上帝的子民丟下了炸彈,炸毀了十字架。
至高無上的上帝,已無法看清楚這個他不熟悉的世界。
以色列曾被恨的風暴屠殺,如今再以恨的方式復仇,而且是趕盡殺絕,沒完沒了,長期戰爭,一直擴大。但不論以色列開了多少條戰線,他們永遠不會忘記加薩,「那裡還有未殺盡的敵人。」
深夜,我閱讀《紐約時報》報導,再追查之前其他新聞,包括以色列軍隊在約旦河西岸進入電視台,軍人拿著槍封鎖半島電視台,我的痛及憤怒到了極點。
痛:因為達盧和我們一樣,他有身為人的一切權利。他那麼努力,卻在全球注視下,於大火中被活活燒死。
憤怒:我知道這個世界多麼偽善,人多麼自私。在這個世上,最容易生存的已不是蟑螂,而是「不干自己之事的自私人」。多數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殺到他床上,他寧可閉眼假裝不知。
曾有人勸我不要批評以色列,「猶太人勢力太大了,這對你不利。」以色列駐臺代表處曾經希望和我溝通,我拒絕了。回:「等你們的政府停止殺平民,我們再來討論一些事情,否則徒傷感情。」
一位經常上談話節目的朋友,以結構式語法分析:「瘋狂的以色列就會誕生瘋狂的哈瑪斯,瘋狂的哈瑪斯就會使巴勒斯坦人受害。」
我看到一個十九歲的孩子,他和他的夢想被活活燒死,我對這種「歲月靜好淡然式」的分析文字,無法接受。我寫下:國際現實不代表我們需要冷漠。國際的無情不代表我們應該跟隨,無動於衷。
我彷彿看到九年前的庫迪和達盧在另一個世界,在水火中擁抱。那裡有真正的上帝,那裡有真正的神曲。
我很渺小,我年紀一大把,我病得不輕。但我的心還在跳,我依然憤怒、我依然心痛。願你和我一樣。
這個世界的歷史一直是一群人,共同發出怒吼,才改變的。不是蟑螂,不是自私鬼,不是歲月靜好,世界才產生了人道主義、國際法,以及民主。
阿門。(摘自時報出版《如此歲月,如此幸福》;更多精彩內容請免費下載《翻爆》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