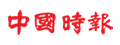一些曲以及歌
寫信ing
「如果要與你共度餘生,那麼餘生越快開始越好」 ~電影《當哈利遇到莎莉》
親愛的大光先生:
好巧呢,你的信上寫老電影《當哈利遇到莎莉》的台詞,問我當時電影確實的中文翻譯是怎樣的?(我怎麼可能記得?)倒是我今天在臉書上正好看到有臉友提及。(那個,那個,怎麼有點像跳坑的樣子,不過,我們這樣信寫個來來去去,也可以算「共度餘生」吧?「一起過人生剩下的老年日子」而且,我們已經開始了。)
這電影不算太老,有天有朋友問我:「有部講Benny Goodman的電影,中文名字記得嗎?」我:「就叫斑尼.固德曼傳啊。」
那是我唸小學時,父親當時的「階段性」朋友大約是向他提及了,他很當一回事地把我由學校接出去,步行到新竹的「樂民」電影院看了《斑尼 .固德曼傳》那是搖擺樂之王。陸軍軍官的父親和小學五年級的我,去看了這電影,家裡有收音機,但父親從不曾收聽音樂,年輕時父親會唱的歌只有黃埔校歌和兩種不同曲調的「滿江紅」。「搖擺樂(Swing music)」應是他的「份外」音樂,他後來也不曾在收音機裡搜尋音樂,但搖擺樂卻成為了我的音樂花圃中一顆先到的種子。
我對音樂是一種「盲知」,喜歡哼唱喜歡聽,卻記不住音樂知識,雖然音感還不錯,但古典音樂、流行歌曲都能接受,是很被其他愛音樂者看不起的,我也無所謂。
有一個印象,是四歲時?媽媽去台中的婦女會開會,因為距家很近,她走一小段路就能回來看看我,所以便放心的把我一人留在家中,我呢?快樂地去抓出一瓣蒜瓣,剝皮,用小匙切半,用蒜汁去沾黏媽媽掉下飾片的耳環,待乾,媽媽就能戴這白色的美麗耳環出門了,(誰說的?)我是耳上戴著綠色那付完好的夾式耳環做這工程的,當然,腳上穿了媽媽紫紅的麂皮高跟鞋。
有一天被不放心而回來探我的媽媽抓個正著,她大聲說:「不要唱這個歌,不要唱這個歌。」媽媽小眼圓睜(我們家一屋子小眼睛)「小孩子,怎麼唱這個。」當然是跟她學的,據媽媽後來說,我唱的是白光的〈牆〉(《626間諜網》)我媽會唱白光全部的歌,我便也差不多會唱白光全部的歌。是,唱歌對我很簡單,曲調不會錯咬字清楚就行,才不管什麼意思。我喜歡我媽媽唱歌,她的聲音好聽,而且唱歌時她是全然心情放鬆,無法罵人的。(啊,你唱歌嗎?你媽媽的聲音你記得嗎?)至於〈牆〉不准唱是因為歌詞有「人家鴛鴦同羅帳,奴家有夫不成雙」這個,也是長很大才懂得的。
曾經有一次,幾個朋友出門去山裡走走,山路高高低低,見鬼了,女生都穿了有點高跟的皮鞋,幾個男的朋友看眾女生的裝扮只好唱唱歌分散生的氣,(他們事先又沒說要走山路)他們唱:
這綠島像一隻船,在月夜裡搖呀搖,姑娘喲妳也在我的心海裡漂呀漂,
讓我的歌聲隨那微風,吹開了妳的窗帘,讓我的衷情隨那流水,不斷地向妳傾訴。椰子樹的長影,掩不住我的情意,明媚的月光更照亮了我的心,這綠島的夜已經這樣沉靜,姑娘喲,妳為什麼還是默默無語。
哈哈,〈綠島小夜曲〉嘛,我們小時候的歌,歌詞呢?抄歌詞來,因為有的人記不全歌詞。邊唱邊抄歌詞的人也出了題:「把我愛你歌詞寫來換。」我愛你?幸福合唱團嗎?什麼啦,是〈你願意不願意〉
我要對著你說我愛妳,讓你的幻想份外美麗,你的眼睛早已全告訴我,
你要我愛上你。我愛妳,字眼是那麼甜蜜,出口是那麼容易,我一聽就歡喜,啊,我要對著你說我愛你,你願意不願意?
我們爬哪裡的山,男生四、五人女生四、五人,都是誰呢?全不記得。後來去吃了館子,吃的什麼呢?也全不記得,可是唱的歌抄歌詞的只有這兩首,記得好清楚啊。
我這一輩子斷斷續續做過很長時間的播音員,挑選的廣播用音樂與歌曲有大盤帶式的錄音帶,也有33轉的黑膠唱片,後來進步到彩膠的小唱片,每當看到兒時、青春期或三、四十歲時接觸過的音樂、歌曲名單,都有 一股驚喜,就算當時節目中不使用,也要帶到錄音間去,一個人靜靜地把舊時的音樂和自己關閉在小小的錄音間,用微笑或默默流的淚去回憶曾經的人生。
下次,大光,下次多和我說一說你,好嗎?有時覺得我和並沒有很熟悉的你把自己說得太透,有點不好意思,你讓我多知道你一些。可以吧?
(上次你寫了你的朋友「溫育人」還沒寫完,這是他的真名嗎?)
祝福健康快樂(這不俗,這是最重要的,沒有更重於健康快樂的事。)想念。 愛亞 2019熱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