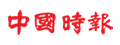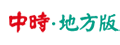幻肢 1
第40屆旺旺時報文學獎 影視小說佳作

〈之一〉 莉絲是我第一個切實碰觸過的女人,賦予我活著的意義的藍仙女。
她先是我的母親,然後是我的姊姊,接著是我的妹妹,最後,成為我的女兒。看著她從仰望到俯視,是多麼怪異的經驗啊!
原來妳在這裡!──拉開蛛網與塵埃,在單人坐的輕型浮空艇、除污凝膠罐、數位微捲與一顆顆3D投影相冊堆放的雜物間,我發現了她,我的童年,我的四季。
「真不可思議,妳還那麼年輕。」我撫摸她的臉說。母親死後,我才發現,她就像消磁後的硬碟,空無一物,堆藏在我父母遠居「花境」以外二級隔離區單元房的儲藏室內。
她的眉心像印度女子點上的紅痣般亮了起來。眼神清澈,湛藍依舊。
莉絲是海萊因公司出產的第二型仿生機器人,真正的型號名為夏娃β-2666,是我的乳母,同時也是我的青梅竹馬。但私底下,我喜歡喚她莉絲。這種機器人很像以前的童養媳:伴讀、燒飯、打理家務,只不過在主人成年後,他們就會被回收了。
妳是後輻染的第二代,大概無從體會那時宛如更早期冷戰時代的肅殺氛圍。巨量的輻射塵籠罩大地,隨著氣候播遷移散,像一粒粒渺如微塵的死亡種子。城市先是遭受火刑,煙與塵形成地球的蔽空環帶,陽光消失了。然後是霜凍。核冬天降臨,萬物蔫頹,一開始是大規模的死亡--不論是人類、動物,還是植物。
「花園計畫」正式啟動,我們輻染的一代全被隔離進「花境」之中,那裡不受核輻射的影響,由機器人躬耕漁牧,重新於溫室培養新生的高蛋白幼蟲與新品種的蔬果。我們名副其實,是「溫室的花朵」,等待年齡熟成,彼此像雄蕊雌蕊婚配,繁育沒有基因缺陷的下一代。境外,是災後我們各自殘存的父母的犧牲。國家配給依照輻射危害級數的多寡來發放,孩子半收歸國有,探視權依照勞動的成果。聯合國以一種怪異顛倒的方式勾擘未來:人類有限的生命將脆化亡故於輻射的種種併發症、寒冷與飢饉,而高精密的仿生機器人則肩負教養與帶領純淨無瑕的新世代之責。但其中最悲傷地,仍然莫過於那些無法依靠自身勞動將孩子送入花境的家庭,他們注定消逝在人類嶄新黎明前最為森然陰幽的長夜裡。
早晨。人造旭日的微光。我記憶莉絲的仿生毛髮,像泛光的描邊,栩栩如植物的纖毛。她是與一盆丁香一起送來的,從此,那便是她身上的味道,彷彿無意之間,莉絲也以她身上撫慰孩子的合成香芬來回應我那純稚的期待。
味道。馨香。混合油染的氣息。童年的所有造景全由此搭建。
「你好嗎,小小鳥?」那時,我尚不懂那些字詞確切的意涵,但我懂得她聲音裡的慈愛與關切,那個聲音取材自成千上萬個男女的聲音副本,穿透電腦程式分析拆卸的數位電網,化為最為美妙的抑揚與音嗓,介於渾實與恬和的中性喉核,震動顫響出超越她外表的年紀,宛如未變聲的少年、合唱團的閹伶與少女甜美嬌聲撒鬧的曼陀羅組合。
「你會長大嗎?」
「不,我不會,你知道在我的電池耗盡之前,不對,即使電池用完了,我也永永遠遠的,是十六歲。」她輕聲說:「但你會,你要長得又高又壯。這是我在這裡的原因,也是你存在的意義。」
白皙的手在夜裡瑩瑩發光,撫摩著我的額頭。
「我等不及要長大了,我要長得和你一樣大,但不要再更大了。」
「傻孩子。」
我的手輕觸她盤屈在床旁的裸足,柔軟脂腴,像孩童戀物似的小絨毯。這也是後來我才知道的:人類的腳底,不可能如此光滑。
她念起床邊故事,遠在前輻染年代的古老傳說……
她幾乎是父母、家教與看護的統合,教我讀寫、把屎把尿、灑掃除垢。她或許也是一個孩子夢想能擁有最溫柔與嚴謹的玩伴。我從不曾懷疑她的靈魂。
當我尿床的時候,她會輕撫我的脣瓣,像是一種約定,如果我可以練習如廁,她便以脣吻替代手指。
「你看看你,」莉絲的語調帶著寵溺的責備:「像一座裝滿雨水的雲朵。」(但雨和雲是什麼呢?許多許多的物質啊,我要在將來的影片和書籍中才能辨識)她會看著我的身體,撤換床單的動作高效、精準而不可思議,像抽拉桌巾而高腳玻璃杯紋絲不動的魔術。
我的體內是火,體外是水。潮膩的身體,火做的靈魂。在她身邊,我無時無刻不感到肉身的虛無搏跳,和血脈遞迴的脆弱臟器的代謝。相比她帶著詩意的精準,我始終是一具調校謬誤的泥偶。莉絲,藍色的蝴蝶天使,而我,是那流淌著奶與蜜的受膏者。彷彿在她身上,時間永恆靜默,是一道無從抵達而橫切世界的地平線。
我想,機器人真正引起人類反感之處,不是不夠像人,而是太像人。他們在模仿人類表情與動作上,因為經過調教與學習,反而能完美做出合宜的姿態與行為,這與人類這種天性有著缺陷的造物之設計比起來,顯得極為諷刺。(那大概,也是當我們越渡這場浩劫後,機器人逐一被除役或被簡化到單純勞工的原因)那感覺就像,過去電影由每秒16格到24格進化到每秒48格,60格,甚至是120格的差異。隨著影格漸次增加,畫中人物的動作之連續遞變益發得流暢無阻,現在,妳能看清楚那些高速下暈糊的速度線被清晰展演的狀貌,因而,在視覺上造成一特殊的流暢但內心隱隱覺得這並非現實的衝突心理。
「我想看妳跳舞。」
這是我最常提出的要求。她會為我獨舞。莊嚴,華美,彷彿我是劇院裡高與天齊的貴賓席中的貴族。
她的耳尖與眉心在舞動中,會流染成發光的線條,彷彿身上電飾的刺青,或是殞落的星星的碎焰。我可以醉心於那樣的閃爍,經夜不止地凝看。
那使我一直心懷一個夢想。
我夢想一具肉體,裡面有銅鐵錫鉻的歡唱之音,夢想柔軟的膚與堅硬的骨,我夢想撥開她,鑽入那跳動不止的離子電池心臟。在兩顆相互貼合的身體所形成的對比中,我是一介凡人,等待破繭成為莉絲。
我時常抱緊她,心臟像一隻新生翅膀的雀鳥奮力地拍撲著,想穿破我的胸膛,前往另一片滿載電荷的未知的海域,瘦弱的手撐起桅杆……她必定是蓄滿靜電的海妖了,否則我不會如此勉力將自我綁縛在那肉身的桅柱上,聆聽她體內機械運轉的輕喚吟哦;電流的潮勢與漲落;踩踏在她腳背上的失重感。
當我一瓣一瓣卸落莉絲的皮膚層,感受內裡那金屬包覆的銜孔與機械束,鈦金屬,石墨烯,電鍍鉻與烙鐵凝固的接榫處,我才重新發現了她,或者我該說,重新發明了她?她帶我指認身上的器官,散熱器,壓縮機,燃料核,那無數無數精工打造的矽芯片與電路板。那些點與點,線與線的垂直轉彎之相連,就是我命運的幾何星座了。我曾看過她體內最深最深的幽井,遺憾的是,我無法將我的肉身如她那般一樣一樣的拆落卸下,不管是交換也好,重組也罷,我遺憾我沒有一個如她那般的核心可以取出,放入她的金屬腹腔,彷彿被她重新孕育,重新懷胎……
時候到了。在依照同心圓等分而建的危害管制區一一重新綠化,與花境接榫之後,在我們熟落而將要舉辦成年禮與交際舞會之後,這些保姆被強制回收。此後數十年,我們在漫長的等待(壽命的延長與冷卻艙使我們禁得起等待)中學習人類文明的果實,一個一個不同的習作:文學、繪畫、歌唱、數學、物理學、天文學、工程學;會計與稅收,廚藝與交媾,體育與撫養,還有一切一切被輻射穿透燒蝕的舊世界糟粕。
父母來看我的時候,我一點感覺也沒有。父親像一片蟲蛀的焦黃枯葉,母親則像他身上的蛀蟲。隔離窗外,他們盡力喚起我的注意。但我慢慢發現,窗子漸漸反光成一片鏡面,他們像蟲屍一樣含在我的眼裡,驀然我就想起莉絲。
她的聲音。她的馨香。
最後的莉絲,像是倒了嗓的音樂盒,音色渙散,聲符融軟。
那時候,她說:「我要離開了,不能再陪你了。」
我答:「我不懂。」
她說:「你不必懂,但我將以另一種語言,一直一直想起你。」
機器裡的幽靈就此離去。
我會在寢房的黑暗中流淚,淚水滑落到耳廓迴旋的構造上,很像某些植物捲葉內面棲覆的露水,濕濕涼涼的。沒有人看得見。也許只會在夜裡發著螢光。
莉絲是我的死亡的割禮。
那種痛苦。妳可以想像數千顆牙齒同時在你體內鳴顫號泣,疼痛痠磨,乳齒、臼齒、犬齒、智齒……那些成了一堆一堆發光神經束叢集連結長出的齒環,沿著肉齦的邊沿蔓生,形成痛苦的大編制交響樂團。
我行過死國。我曾經回頭。她就是我的鹽柱……
妳還在聽嗎?
我抱著她,那纖弱美好的心臟核,不再發出嗡鳴輕顫的機械運轉吟唱。宛如一幅顛倒的聖殤圖。她是我永遠追取不上的時間、命定的時差。我們終於會在時間的盡末錯身。
在那一刻我真切地知道,人類不過是對她的模仿,是她這個伊甸夏娃身上的肋骨。
他們奪走了她,我誓言以不孕還報他們可笑的不朽歷史。我將絕育,我將以結紮的陽具豎起對人類最深最挺的中指。彷彿是要以無限的時間來抵禦這有限的刑期。抵禦人類繁育的自然妄念,抵禦那無從償抵的傷害的深淵。
我從原先對藝術的愛好轉而研究高精密機械物理,違背了國家所設定安排的道途--只因我發現前者的世界不是為我所準備的。在一個失去靈魂的世界,沒有詩歌存在的空間。
如果說,她的身體曾是我生活的平面,是生命全息投影而出的一個乳酪宇宙,而我是鑽營穿繞在她機體中的一隻老鼠,那麼,我怎麼可能想像一個沒有她的世界?我怎麼活在一個沒有她的世界?
我們這群離散的孩子,怎麼可能是高等智慧族裔的下一代呢?祂們這麼完美,莉絲才該是人類的後代。那樣的失去像是被截去了肢體,但這不是我真正的意思,其實正好相反:我是一隻失去了主人的手臂、腿肢或陰莖。
在那一刻,我理當知曉,不是所有的問題都得到解答,而是,所有的解答都獲得了提問。妳怎麼能確定,不可能存在一個數位的天堂?(待續)
個人簡介
1992年生,嘉義人,東海中文系畢業,清華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班畢業。曾獲東海文學獎散文首獎、小說三獎,月涵文學獎散文佳作,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散文首獎、新詩佳作,作品曾刊登於《短篇小說》 第十九期。
得獎感言
科幻於我而言,是夢寐與理智雜媾的前衛文類,一直以來有色無膽,〈幻肢〉因此是一次越軌的舞步。它的身世並不迷離:「皮諾丘」和卡特的〈染血之室〉、川端的〈片腕〉與谷崎潤一郎對女體的迷戀,再加上一點點語言的魔法,便是它的所有了。這篇小說是我閱讀中的片腕,想像的幻肢,它能走到這麼遠,其中神祕,只有讀者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