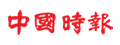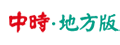晨間漫走
家常書寫

「溪水急著要流向海洋 浪潮卻渴望重回土地」──席慕蓉〈七里香〉
金黃晨光照亮田間千萬露珠,放眼望去彷彿稻穗已抽長,但其實秋分剛過不久,稻作還青綠,離收成還遠;光影錯落的稻綠間,晨露宛若天上掉下來的星星,在稻葉上瑩瑩閃閃,大珠小珠都剔透,稻田裡開滿晶瑩之花,往天邊延伸。清晨,我踩踏鄉路,蹲在田邊,走看田野,做功課般。每次回來,也許一大早,也許傍晚,總要這樣走它一回二回,否則,宛若回家的功課沒做完。
架設在小時候抓蝦摸蜆消暑的渠上、堂嫂家的雞籠裡幾分躁動,體型最大的火雞咕嚕咕嚕拉著長音,彷若提醒主人有人靠近喔。不遠處的亭仔腳下幾個人在聊天,我趨近時,點頭問好,然後互點名字稱謂來。
「遮咧是……,彼咧是……,我是……,你是……」離家超過四十年了,我認識的就只剩幾個都八十以上歲數了的、與父母同輩的老者,而他們之中還認得我的少之又少了,總角交則大都多年不見,娶進來的媳婦或其子女更是我不識的,而他們也不認識我,走在成長的鄉道,我儼若「在地的外地人」,常得搬出父母兄長的名來釐清自己確是這片地裡土生土長的兒女。
轉入田間路,經過明仔伯家,一隻黃花貓躺在紙板上曬太陽,幾條薄毯在竹竿上輕晃,剛剛已見過九十幾歲仍耳聰目明的明仔姆,卻不見以前經過時總也在門前坐的明仔伯,不知是否在屋內?已記不清何時開始,回來若不再見到哪個長輩,已不敢隨意開口探問;有時不知道反而好,至少還停留在美好的想像裡,免得像昨日那般。昨晚得知勇仔叔個把月前也離世了,心裡幾許落寞。勇仔叔是爸爸親舅舅的兒子,年紀差不多的表弟,年幼時便搬來老家附近同住,以前也是爸爸的蓋屋班底之一,幾個月前我還跟他站在家門口前田角聊天,如今,我著實想不出以後還能找誰探問父祖輩的過往與故事。
茄子大黃瓜吊掛在藤葉間,一二隻黃粉蝶紋白蝶飛過,一株虎尾草擎著花序獨佇稻田旁,似也和我一樣想著些什麼。遠遠望去,遠山飄渺倚靠天邊,向它們的方向走去,就是三嫂時時牽掛的火龍果田。
火龍果田裡,尖刺張狂的莖枝交錯互疊,小綠果在光影中奮力茁長,幾顆熟裂的紅果高掛莖端,更多散落於田土,從田邊看去,那股紅透在田綠中亮眼極了,卻教人感受不到豐收的喜悅,而是傷感與惋惜;二三朵大白花,彷彿不按牌理出牌的叛逆小子,執意捨棄傳統地背棄夜晚、迎向陽光,以嬌美以細緻招引蜜蜂,吸引我往莖刺裡鑽去。
絲瓜花咸豐草花黃白相襯,福壽螺卵綠稻稈紅綠相間,我拿著手機到處拍,田裡的田外的。忽然一陣機車聲傳來,我回頭看了一下,幾分鐘後便往芭樂田走去,往裡喚著「阿嫂」。裡頭的人手扶斗笠撐開枝葉,探頭笑問,「遠遠看一咧人跍佇遐翕來翕去,原來是你喔,你當時轉來?」堂嫂,一個個性溫婉的女子,嫁給我們公認手足裡脾性最好的大堂哥,相夫教子,侍奉婆婆至孝。但老天並不護她。多年前,當郵差的堂哥在一次執勤途中,被停靠路邊無預警突地大開的車門奪去性命,留下四個子女、老母及走不出傷痛的她,徒留唏噓。
往溪邊走去,過小橋,回望邊坡,以前母親種植的竹欉依舊。再過去是幼時收成香蕉、稻作與番薯但如今已然消失的田野,只餘回憶之地。
以前,我也曾是詩人筆下急著要流向海洋的溪水,這些年則是渴望重回土地的浪潮。三哥離世後,我深怕三合院總有一天會頹敗,曾動念買下老家,重新整理,但產權的紛雜、我對進步醫療的依賴……諸多現實問題都不是我能克服的,只能想想就好。
雖然北居時間早已是鄉居時間的兩倍有餘,但若問我哪裡人,我的回應從來都不會是台北人,而是這片十五歲就離開了的、童年根長父母曾在心靈歸屬的地方。
入了家門,三嫂問我,「猶未食早頓,去佗位?」
「去田裡看看咧。」我說。
而我沒說的,是藏在心裡的、對這塊土地的不捨與眷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