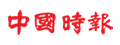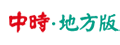巴哈無伴奏
人間書摘

我和女孩見面的時候,她說不要學樂器,只要聽故事。很多很多的音樂故事。
我們第一次碰面是在我的琴房裡。女孩知道我是拉大提琴的,地上也散亂擺放著一堆大提琴的唱片。她希望我講大提琴的故事,一些透露著陽光 、雨和霧的故事。
女孩聽過巴哈,但女孩沒聽過《巴哈:無伴奏大提琴組曲》,至少她是這樣以為的。當我放上第一首,樂音飄起才幾個小節,她馬上就認出來,那是她就讀大學時,圖書館每晚定時播放的晚安曲。
「原來是這首。」女孩領悟了什麼。
我告訴她這分珍貴的曲子,原被遺忘在歷史之中,偶然被卡薩爾斯找到,才得以在上個世紀奇蹟似的復活。
女孩的神情顯得愈來愈有興致,好像她真的喜歡這個故事。
「如果妳來了,聽這樣的故事有所啟發,高興地覺得今天並無白過,並給了我一小時一千兩百元的學費,我會覺得自己很可恥。」
「可恥?」女孩失聲的高音,在一片大提琴的低鳴之中,聽來格外嘹亮。
「因為妳值得聽第二個故事。」我一邊說,一邊放卡薩爾斯受甘迺迪總統邀請,在白宮音樂會的歷史性演出。
聽完CD的演出後,女孩的興致降到冰點。我一點也不覺得意外。
「生平第一次聽這場演出的CD時,我也覺得沒什麼稀奇。直到我聽了我老師的黑膠原盤,才恍然大悟。如果可以,妳願不願意和我再重聽一遍?這一次,我們聽黑膠。」
我答應多出來的這一段重聽時間不多收費,女孩只說那不打緊,儘管放就是了。
我緩緩地放下唱針,一切如命定的儀式進行。樂曲結束的幾個小節前,傳來啜泣的聲音。
女孩也清楚地聽到了,她問,為什麼有人在哭泣。
「那是卡薩爾斯演奏的《白鳥之歌》,全曲以他的家鄉加泰隆尼亞的歌謠為基調。因為戰亂的緣故,離開家鄉時他還未成名,如今他在異鄉貴為上客,受邀在白宮音樂會演出,歷史肯定會記上一筆。思鄉的老泰斗,此刻拉著鄉韻,腦海播放的都是兒時情景。那又能怎樣?故鄉是回不去了,他只能作夢或掉淚。我們不知道他午夜夢迴那些愁思的顏色,但透過錄音的回播,我們的的確確聽到有一個人,雖然看不見,卻無比真實地在我們面前,用他的琴唱歌給我們聽。他的啜泣是那樣微弱壓抑,此刻聽來,卻又巨大地敲著我們的耳膜,撼動我們的心。」
女孩淚流滿面。
我知道她聽懂了,於是我說了第三個故事,也是最後一個故事。沒有陽光,沒有雨。而這裡,到處是霧。
我向女孩承認,我不會拉大提琴。
我說,我以前可能是會拉的。但現在,完全忘記了。
我跟女孩說塞拉耶佛大提琴家的故事。在戰火的煙霧中,一個置生死於度外的大提琴家如何支持著音樂的信念,在傾圮的碉堡和塵土掩蓋的巷弄間,不斷演奏撫慰人心的曲子。
「大提琴家沒有死。我去找他的時候,他放的就是卡薩爾斯的這場白宮演出。我想妳可能已經猜到,他是我的老師。和老師相處的時光並不長,找到他之前,我已經是國立交響樂團的首席了。但在老師面前,我折服訝嘆的不是什麼高超的琴藝,而是他那樣悲天憫人的胸襟,那是我怎樣練習也達不到的境界。」
「不知不覺中,我漸漸地喪失彈奏的能力,也無法視譜了。老師發覺情況不對時,已經太晚。自認阻礙我前進深化,老師情非得已,只好把我趕走。我們深深擁抱,以為餘生再也看不到彼此。」
「臨走前,老師為我演奏一曲《巴哈無伴奏》。老師說,我的技巧非常優異,甚至比他年輕時還好,但從我的琴音,聽不見恨,也聽不見愛。事實上,是什麼感覺都沒有。像是有什麼東西封住了我的內心一樣,而那可能正是我失去演奏能力的根本原因。」
「而今晚妳來了。」我跟女孩繼續說,此時我已幾乎淚不成聲。
「妳來了,妳跟我說,妳不要學琴。妳只想聽故事。起初我覺得妳可能只是什麼被慣懷的千金大小姐,不肯努力,卻想透過清談冥想搞定一切。但隨著我跟妳講的每一個故事,妳都能溫柔地接住它們其中滿載的人生意符,不知怎麼地,好奇妙,我發現我苦練一輩子也達不到的那種力量,慢慢充盈我的全身。」
「那即是,我在心裡燃起一種強烈的渴望,想不斷地向別人講一些故事。如同卡薩爾斯透過眼淚講述鄉愁,我的老師曾用琴音向戰火裡的靈魂傳達愛與寬容,我發現我也能說了。」
「最重要的是,我想說。我非常想說。說大提琴的故事,說他們的故事。然後,我的故事。」
●
這是我先生的故事。他人生到此,所有美麗與哀愁。
謝謝你們今天來參加他的告別式,這對一個中年突然銷聲匿跡十年又復出的大提琴家來說,人生下半場的二十七年還能有你們無悔的支持,真是上天最大的賜予與恩典。
他的故事,今天我幫他說完了。
他曾經說,他遇見我的那一天,啞了十年,他終於能夠開始說話,開始對人生有所感覺。他要開始說,用音樂說,用大提琴說。有一天,當他離開,他只有一個願望,那就是,我也要開始說自己的故事。
是的,我就是那個女孩。
我終究沒學會大提琴。卻提早學會了愛。
(本文摘自《瓦力唱片行》一書,寶瓶文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