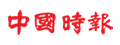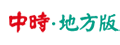之後書

L,現在是台北時間早晨六點四十四分。我在五點十三分的時候便醒來了,奇怪的是再也睡不進去,明明下午還有工作要跑,但此刻我內心有股衝動,極想寫信給你。
清晨的城市是藍色的,不是鴿羽那樣清澈粉嫩的藍,而是某種晦澀的、曖昧不明的藍,青灰色的雲層背後彷彿隱藏著某種雷的預感,籠罩著每個行路之人。
我喜歡早晨,早晨讓我感覺這世界假似又擁有了某種平等。每個剛剛脫離睡夢的人都是一樣的:頭髮凌亂、眼神渙散、腹內空洞而情緒不佳。看那些走在街上的人們就知曉幾分:他們或拎著紅白塑膠袋,袋內裝著油膩的廉價餐點,或夾雜一兩包長壽牌香菸,穿著破舊的汗衫短褲、趿著拖鞋,雙眼迷濛著平庸的夢境的遺緒。
班雅明說過:「早晨不要空著肚子說夢。在這種狀態下,醒來的人實際上仍然處於夢的魔力之中。」每個重複醒轉的早晨,在飲下一大杯冰咖啡和吞食尼古丁之前,我也總掙扎於擺脫那轉眼成舊的夢的殘片,它將我往某個方位拉扯,心思脫離肉體飄遊虛空,彷彿睜著眼睛在自己體內逡巡般地夢遊。
我是多夢之人,夜復一夜的造夢者,那些夢境已然無可言詮,像海邊的篝火,燃燒完畢後再不具有本來意義。那些光焰與熱風、彼此追逐的焰舌,儀式結束後,一切燦美恐怖皆成空無。
像我們這種人,總是做著某個大夢,像私密的織衣揣在懷裡,僅偶爾和信得過的人淺淺淡淡地提起。年輕時,我們夢想著年少成名,等到多年的嘗試以後,我們仍舊心懷失敗而不由衷地嚮往著功成名就。像我們這種人只能不斷地不斷地寫字,要把臟腑血骨都嘔出來化成文字,讓世人看見──但他們究竟看見了甚麼?這一點我和你都沒有把握。我們只知道自己體內有一朵碩大夏花,幾乎占滿骨骼間的每處縫隙,當那花恣意無忌憚地兀自開放,你亦無把握如何掌控那馥郁毒香。
你離開的時候已是冬天,十一月的色澤如凋萎的鳶尾,空餘一份美麗的幻覺。我整整昏睡了三個晝夜,不食不飲,貓在我腳踝旁打著圈子,我只是將自己深深地沉放於床枕,偶爾行屍走肉般起身餵貓、添水,恍恍惚惚地抽著菸,然後便又昏昏睡去。
我不知道要怎麼樣自己才能活得過你。初識你的時候,你相對豐滿而我極度癟瘦,但那時我便知道你已病了,即便你青絲披肩、面頰潮紅,一雙水靈透亮的貓眼總朝這混濁之城斜乜以對。後來,我們曾一起去過大稻埕霞海城隍廟,那時你身型已削減了好幾分。你穿著素白T恤牛仔長褲灰球鞋,像一片被風忘記捲走的葉子,輕輕盈盈地落到我面前──那是六月或七月罷──總之是蟬鳴綿延的夏天,我們頂著炙陽一路從捷運站步行走去,大廟飛簷,堂宇之中神祇低眼,慈悲俯身向芸芸蟻生,你在巨大的燦金神身之前垂頸合掌,無聲默念良久良久。我則在平安符攤位前流連,挑了好幾只不同款色的符包:櫻紅赤金豔桃盈盈握在手心,好像便擁有了健康財富與愛情──L,我猜你仍舊心懷愛意,向著某人──或者純粹向這紛麗又荒蕪的滾伏紅塵,因為你笑著從我手中抽走那枚桃瓣色的符繩,微微歪著頭說:「這是給我的對嗎?」我不知該說對更不能說不對,但我該如何去想像,你置身這般景況之下,懷中尚且猶抱著幾分愛的可能?
我們都做過關於愛情的大夢,那麼薄那麼軟那麼柔軟易破,像一個被吹脹得過大過圓的氣泡,朦朦朧朧地罩住了大半座城市。氣泡裡的人懵懂地走路、進食,親吻與擁抱,牽著以為將永遠牽下去的手,並著以為要永恆偎靠著的肩。但你應該比我更早地看透了這一群瞬眼電露的傷心眾生相,和一路行來磕磕絆絆的顛倒夢想。你應該是置身氣泡之外者,一心清明剔透如冰石如水玉,但你從未返身背對一切,而是一往無前地投身浪波間,多麼無謂又近乎無畏。我想我和你最大的不同,就是我沒有你的勇敢──在這世界離棄你之前,把自己先行抹去刮除的那股勇氣──換言之,我無法對自己殘忍,你卻如此懂得決絕與乾淨。
L,你走之後,世界好像歪斜了幾吋,又似乎一步也沒有移動。黑壓壓的人群每日每日踏著長長的馬路,從城市的一段流徙至另一端,從一間房挪身至另一間房,彎著頸子不抬眼瞼地敲著鍵盤,儘管整片窗景就在他們眼前毫無防備地展開……我領來的小貓常蹲在窗沿看風、看樹,看午後的光影如何緩緩地洗過一整條乏人的闀陌。有時在失眠的深夜,心緒千徊萬纏,滑開手機看見你在訊息列表中閃著上線的亮光,反覆廝磨語詞之後卻仍僅僅敲出「最近好一些嗎?」你總是淡淡地說道自己好多了,快要好起來了,我也就真的這麼相信了,即使我從頭到尾,全然都是錯的。
你離開之前的那段時日,你將自己密密地縫成一隻口袋,所有的病鬱糾愁全都鎖起不讓人窺聽,唯有當你願意時方才從口袋中稍稍探出頭,像一隻靜黠的貓咪,露出一雙靈靈眼瞳咪嗚而來,比如去年秋天我們約在咖啡廳碰面,你便得更瘦更薄像一紙玉蘭花瓣裁壓的人形,我想起你養的白肚虎斑貓,經常在IG上看見牠蓬毛袒腹、瞇眼沐陽的無憂身影,但總感覺一旦問起了貓就等於在問身後事,遂聊些日常的牢騷話,描點著那永無指望到臨的模樣完整的感情生活。「沒有愛我沒辦法寫。」忘記這句話是出自誰之口了,我記得你怨懟著語言的不可信,以及由語言的曖昧溝通的斷裂所引發的一干炤情小恨,我們一邊輕蔑著數落著寫字的人,個個窮得脫褲又雞腸鳥肚,心底卻十分清楚,文字是少數我們能捲在舌底切切實實吸吮吐哺的甜蜜。若不能再寫,你亦寧可不要再活。
這原本該是一封充滿後見之明的信,並想著也許你會好奇之後發生的事情,但我愈來愈覺得困惑且無甚可言說。我只想說從去年冬天之後,我仍舊經常地想起你:聽歌的時候,搭車的時候,打開紗窗對著戶外柏油路的蒸騰熱氣抽菸的時候,或者,在捷運站出口碰見叫賣玉蘭花的中年婦人的時候……在濃稠如湯的夏日傍晚的空氣中,我經過那名賣玉蘭花的女子身畔,一縷特別濃郁的香氣攫住我的衣角並尾隨好一陣子,久久不能夠散去……甚至在這樣微不足道的細小的時刻裡,我依然想起你來,大約整整十秒之間,我想著你某一次輕巧拋來的彎眉和笑眼,像玉蘭花的氣息,擦肩之後又無預警地襲來,在近乎靜滯的黃昏天光下,與人們背對背地、悄悄地走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