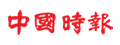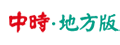聲音
家常書寫

記得那年我還年輕,像匹小馬騁馳在職場上。我總是將頭髮剪至及肩,穿上緞面白襯衫合身套裝,鎮日滯留在燈火通明的辦公室戮力地工作。
父親已罹癌多年,在經歷數次療程後更顯憔悴。凹陷枯槁的臉,細瘦的四肢套上藏灰色呢絨夾克,像顆漏風的球,正為著即將歇業的公司善後收尾。
我與父親感情極好,我們常在睡前閒敘。父親喜愛穿著那套鋪棉老睡衣,坐在高背搖椅上與我對談,他的咽喉因治療的關係,聲音已喪失了原有的中氣,常發出低沉的氣音。我們的話題廣闊,自工作場域談及生活細瑣、愛情、人生觀,父親總是勉勵我或淘氣地促狹我,讓我常常忘了他是一位患者。
記得那是一個深春的早晨,我接到母親的來電,得知父親忽然渾身無法動彈,已被送入T醫院急救。我隨即請假飛奔至醫院探視父親。T醫院急診室猶如一座密閉的防空洞,人聲雜沓,門片開闔病床滾輪鏗鏘碰撞,我在角落的橘色拉簾內找到了他。醫師告知我們,父親因癌細胞移轉侵蝕脊椎與呼吸道,已導致全身癱瘓。父親意識仍清楚,只是再也不能行動與言語。瞬間雷光閃電般將世界剖為二半,昨夜父親的聲音海浪般在我腦中拍打。
幾夜後,父親被轉至普通病房。他的頸部氣切後接上長長的呼吸管,全身螫滿粗細管線,連接至各型機器發出低頻規律的聲響。父親的世界至此縮成一個點,墜至深井般的底層。看著父親巨人般倒下,我心中的未爆彈猛烈地炸開,昔日商場活躍的父親,彷如無法再啟動的汽車引擎,山一樣地崩塌,成為一支無聲的影片。
當時SARS事件爆發,人人自危,疫情於全國蔓延肆虐,許多醫護人員相繼殉職。
那日下午,父親突然高燒不退,經過醫療團隊診斷,有疑似SARS的可能,故要將父親轉至負壓隔離病房隔離。所有醫師與護理站人員需遵照醫院安全指示緊急撤離。
「很抱歉,我們都得離開。」醫生黯然地說。
「我們該怎麼辦?」我疲軟地問道。
「請保重。」這三個字如一個沉重的句點,截斷了我們之間的對話。
又是一次命運的鼓譟,厄運如骨牌般接踵而至,我未曾想過這個僅屬於家庭的悲傷居然與社會接軌。
這時,母親毅然決定要一同進入負壓病房照顧父親。
「都帶回去吃吧。」她將雞精營養品全數推向病房外的我。
母親是個溫柔堅毅的女子。父親奔忙於事業三十餘年,秉性跌宕風流,母親在婚姻中壓抑隱忍操持家務,在父親罹癌後,放下昔日過往盡責地照顧父親。
之後,我與弟妹們亦被居家隔離。
在這空蕩蕩沒有父母的老房子裡,書桌上父親的日記本,白瓷馬克杯,母親懸掛在廚房入口的舊圍裙,絳紅長大衣,光亮厚重的餐室吊燈,深棕色大門,各自孤獨的凝凍於老位置上。在這尋常熱鬧的家,像是突然熄滅的燈,闃暗的廢墟,等待著黎明天亮。
我思忖著,蟄居在仄小的負壓病房裡,猶如一座與外界斷裂沒有出口的深洞,被層層消毒藥水包覆,所有的聲音俱消匿在每則縫隙裡。在那只有彼此的空間裡,失語、無法行動的父親是如何面對乖順的妻?在他劇烈起伏的生命中,疾病之於他除了疼痛,還有什麼難忘的風景?在我們之間促短的歲月裡,他還記得那些甜蜜與痛楚交駁的時光嗎?
一個月後,醫生來電告知父親已被解除疑似SARS的可能。
再見到父親時,他顯得更蒼老了,日光燈下父親羸瘦的臉龐被刻鏤出立體的陰影,像是我每天以鉛筆寫下的日期這般黑漆。那些漫長的等待,那些風雨,那些傷害,被時光的滾輪一一輾過,餘下相紙般的記憶畫片。
經過了這麼多年,我已步入中歲,父親這二字仍如熱燙的瘟疫盤踞在我的內裡,無以痊癒。那些過去像一只被冰凍的標本,在杜鵑櫻叢盛放時融化,迸裂出寒冷的低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