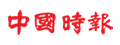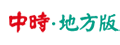不吃花生倒吃花生皮
人間書摘

水煮花生,去殼剝皮,半斤花生只得一小碗花生皮。
花生仁外一層薄膜花生皮,在中醫稱花生衣。花生衣養血補血,具止血之效,科學論點指花生衣有助強化骨髓造血功能,增益血小板數量提升。
有一小段日子,我託小姑姑每隔幾日在早市購回水煮花生。繞口令說的,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我剝花生不吃花生皮,若暉不吃花生倒吃花生皮。
一般人血小板指數十五萬,低於兩萬便會引發自體性出血,腦出血即死,那時若暉的指數已經跌至一萬六。西醫安排固定時間輸血,醫囑定時服用鐵劑或者濃縮棗精。中醫合併照護,每天開立兩包水藥,此外建議以花生衣補血。
換作幾年以前,恐怕我會嗤之以鼻。花生的那一層薄膜欸,當真有效?然而那當下我彷彿沐浴焚香,慎重淨手去殼剝皮,無異敬神儀式。彼時我也真正虔誠敬神。每晚睡前禱告,雙手合十於胸前,黑暗裡我再三呼求耶和華上帝、媽祖娘娘、關聖帝君、藥師如來佛、宇宙大人的名,用盡全副心力向神明祈求說,拜託請讓我妹妹康復起來吧。
隔天日頭上升,世界絲毫未改,我如舊剝著花生衣。
●
花生皮只是飲食控制的一小部分。若暉生病以前,我們從來沒有飲食控制的概念。
或者精確地說,沒有飲食控制的可能。
國中三年裡一半的時間,我們有什麼吃什麼。營養午餐是唯一正常的一頓,晚餐的追求基本是果腹。餐桌偶爾擱著不知道誰留下來的殘餚可供配飯,至少白米飯新鮮現煮。身上稍有零錢,可得張日興雜貨店對面那間飯麵滷味小吃部的一碗麻醬麵。更不濟,張日興販售泡麵一碗十五元,放學省一趟公車錢走路回家就買得起。吃進肚裡的唯有澱粉和熱量,纖維素與蛋白質同樣匱乏。
那時家裡還有阿公。但阿公是一抹幽魂般存在家裡角落的贅婿,自我們懂事以來,家事不分大小粗細,沒有阿公可以過問置喙的一次,連電視遙控器都搶輸一干內外孫子孫女。我們沒想過阿公吃什麼,他也不為我們張羅。
老屋子很大,足夠我們與阿公各自活在兩個時空,甚至足夠給其他人開幾個平行世界,比如長期寄居的大表叔,短暫來訪的小表叔,不時遊走的大姑丈。這家裡沒哪個誰有義務該準備食物,該收拾家裡。
家屋蒙塵黯淡,我們的肉身跟這個家同樣陷入缺乏照養的頹境。
稀罕的一次聯絡上爸,電話裡爸說,「以後有小龍照顧你們。」那就是大表叔,阿嬤的么妹的兒子,我們應該叫表叔,但我們不,直呼他的乳名小龍。電話裡我們沒有力氣發牢騷,不然應該跟爸說,留他還不如不留!
並不是因為小龍只大我們一輪多一些,其時年僅二十六、七。
當時小龍有一輛山葉馬車一二五,三貼載我們上學,遠遠校門口訓導主任面色嚴肅看向我們,小龍說:「你們去跟他講,我是你們男朋友。」又說:「如果你們交男朋友,就打斷你們的腿!」有天家裡出現幾箱鋁箔包飲料,陌生的品牌,我們抗議小龍亂花錢,他說:「拿到什麼就是什麼啊!」我們說你是去偷的吧?小龍說:「什麼偷,是借。」又說:「如果你們偷東西,我就打斷你們的腿。」
小龍沒有工作,跟朋友到處去借東西。家裡四處散落拆解的電視與錄放影機,鑽進家門來去的人臉每次不同。我們從爸的高爾夫球袋裡挑了推桿和S號鐵桿放在床邊,臥房門把懸著風鈴,開門就有聲響。不過門擋得住人,擋不住氣味。有陣子小龍房裡常有異香,味道特別濃烈的那回,我們連日精神亢奮,三天只睡三小時。我們問,如果那是毒,究竟是什麼毒?小龍罵說什麼毒不毒的,又說:「如果你們吸毒,就打斷你們的腿!」
小龍憲兵退伍,講一口外省腔,初初寄居我們老家那時,鄉人多視他是臉龐端方體格強健的美青年。他父親是四九年來台的山東小兵,跟他母親也就是我三姨婆婚後落腳在中壢,生得二子取名振武、振文,盈滿那一代人的輝煌寄望。但帥哥多草包,讀書稀鬆平常,做工沒有出師,賭博技術恐怕只跟我們不相上下卻敢進賭場廝殺,再及染上的毒癮,人生愈走愈是一塌糊塗。菸酒檳榔安毒賭博五毒俱全,肉身點滴崩毀,精神在失控邊緣,我們目睹一個青年的快速下墜,說不出的滿心焦躁與憂慮。其實就是物傷其類,而那時我們並不明白。
我們經常吵架。孩子的我們嘲弄青年的他不幹點正事,小龍總是叫囂:「英雄落魄是暫時的!」我們便每次回嘴:「小孩落魄是會餓死的!」小龍吵不贏,就逃走。偶爾沒有逃走,衝過來甩我們巴掌,抓我們的頭去撞牆。塵埃落定,小龍還載我們去上學,去打一整夜的保齡球,聽說我們遭到同學威脅要蓋布袋圍毆,他一一打電話到同學家恐嚇對方放學走路務必小心。而下一次,我們還照樣吵架。
落魄的英雄喜怒無常,連帶我們日子過得充滿戲劇張力。興起了開車載我們到市區吃飯,一言不合卻立刻棄置不顧,令我們徒步幾個小時找路回家。開心時指天發誓說「你們考上了好學校我買電腦給你們」,嘔氣時就連車帶人停在平交道鐵軌上,等著我們驚慌尖叫對他求饒。
我們懂得應該怎麼表現可以討好他,但我們不。
平交道鐵軌中央我們僵持不下,副駕駛座裡我把雙腳伸到前座平台,鞋尖跟著平交道警示音噹噹噹噹踢踏擋風玻璃,直到小龍按捺不住踩下油門,破口大罵一句:「你們是瘋子啊!」不,我們是快要餓死的落魄孩子。不霉不餿就是食物,止飢卻不飽,慢性飢餓兼營養失調,國三便深陷睡眠障礙,我們還能再失去什麼呢?
小龍根本不是英雄,到底我們也不再只是孩子。不記得哪一天,小龍默默就失去蹤影,如同我們爸那樣無聲無息,而我們迎來國中畢業典禮,走出成功嶺的老眷村。
高職夜校就讀期間的第一年,我們放假還會回家。
彼時阿伯遠赴越南,大姑姑分身無術,爸隱身山林,唯獨小姑姑娘家婆家兩頭奔忙。成功嶺老家豈止蒙塵,頹圮宛如古廢之墓。阿公在廢墟裡面吃喝睡眠,依舊一派自在如紅塵遊仙。神仙不問家事,客廳地板磁磚白色轉灰色,牆壁爬滿蛆蟲,細看一地芝麻般的褐色瑣屑皆是蛆蛹。人蟲共生,善哉善哉。
(過了幾年我們讀馬奎斯的《百年孤寂》,結局那關於邦迪亞家族的預言:「這一家系的第一個祖先被綁在樹上;最後一個子孫被螞蟻吃掉。」忍不住心有所感,莫非拉丁美洲的蒼蠅果蠅並不繁盛?)
那樣的廢墟仍然有人上門。不是爸的債主,就是小龍的。老家大門向來不上鎖,債主自由來去,客廳裡坐看幾個小時的電視,直到確認當日索錢無望而歸。我們厭倦已極,某次聽見債主腳步聲而給門鎖上鑰,表明拒絕往來。孰知神仙有求必應,阿公給債主開了門……
(本文摘自《我家住在張日興隔壁》一書,寶瓶文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