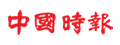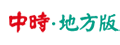一只食碗,在縫隙之處投射出時代縮影(下)
人間書摘

然而,就算清輝窯曾經在小吃業界比同業知名品牌更受歡迎又如何呢?我認為清輝窯早期小吃碗所創造出來的意義,不在於它「也曾是一方霸主」,不在於它是隱形冠軍,而恰恰在於它在歷史定位裡的「不受重視」,在於它於各種「縫隙」(不管是歷史、文化或工業零件)中卓然發展的堅硬底氣。與許許多多在生活的狹縫裡求生存的小吃業者一樣,透過模仿與無數的嘗試,在種種「不受重視」的發展過程中,清輝窯持續前行,成為小吃產業背後的重要配件,直到今天,進一步躍升為新世紀精密科技與工業生產背後的重要環節,卻從來都不是那麼彰顯自我,更多的是幕後服務的姿態。它的身分,某種程度上就像台灣近代史的倒影。
我幾度在福和橋下的跳蚤市場、零星的台灣古市集或舊貨店看過清輝窯的機器移印老碗,然而它們並不如那些五○年代左右的手繪器皿(椰子風情畫、胭脂紅花卉、魚蝦鳥獸等寫意圖騰),受到民藝愛好者關注,箇中原由不難理解。普遍來說,至今民間古物店販售的台灣手繪老食器售價依然親民,除非本身具備了某種難以取代的孤品特質(諸如樣式千里難尋),相較之下,機器生產的絕版清輝窯老件市價更低,通常是銅板價,偶然露面的攤位更多像出清區,而非附庸風雅的骨董器物區。這個置身邊緣的現實,反映了清輝窯在收藏者眼中的「價值」。
在還沒有展開報導採訪之前,我並不介意這點,畢竟在我的眼中,清輝窯在台灣陶瓷發展史中獨樹一格,故事跌宕起伏,並且深入民間,是很有趣的採訪目標,有其無可取代的重量。然而它在文物收藏界的「銅板價」現實,讓我在接續的採訪過程中碰到了另一個慘烈的硬壁─我發現「清輝窯」並不是一個可以坐下來和收藏者暢聊的共同話題。碗盤歷史或文化學者不認識清輝窯,或者說不確定它有什麼特別可以討論之處,文物收藏者喜歡的物件,通常具備有強烈的藝術特質或文化定位。
台灣早期(五○年代至六○年代)曾經產出別具台灣特色與風格的手繪器皿,胭脂紅的釉色、椰子樹風情畫等等都有無可比擬的高度識別度,在世界版圖上足以代表台灣風格,然而在社會經濟結構劇變的輾壓下,隨著生產者與消費者目光的轉移,如此具有台灣特色的器皿已付之闕如。以宜蘭的碗盤博物館為例,其所展出的物件,多半具備了幾個要素:獨一無二的稀有性(手工藝製品或已絕版的技術,比如曾經盛行的黃閃光釉技法)、時代性(當代指標性產物,比如大航海時代產物或特殊民俗用品)與藝術價值。
嚴格說起來,以上幾個特質清輝窯幾乎都沒有─它並非來自於一個波瀾壯闊的大時代,其機器移印技術源自於日本,制式花樣也是仿製日式風格,某些圖樣甚至可以說是粗糙幼稚,加以收藏者通常不傾向收藏大批量產的機械產品,通俗與巨量往往削減藏品價值,貶抑物件在社會文化體系中受到重視的程度,就好像複製畫多半不受收藏者垂青,在炫耀性消費的世界裡,物以稀為貴。
追求與眾不同的細節向來是一門不退流行的美學衡量標準,尚樸的日本茶道愛好者早在數百年前便推崇侘寂之道,珍視器皿製造過程中無心造就的不完美,追求「碗碗有瑕,各瑕不同」的美學,認為每個茶碗的獨特缺陷恰好賦予其無法模仿的「個性」;宋代鑑賞家與文人認為開片(瓷器釉面自然龜裂的現象)最符合審美原則,因為其效果「非人工做作,而是從材質與技法之中自然生發而成。」總之表現形態愈不做作、愈難以複製,愈能表現抽象美學的精妙。
然而,在不同的時空之下,判定「是否做作」的觀點與假設持續修訂,對宋人來說可能俗不可耐的工匠手繪瓷器技法,在明朝官方與文化強權的吹捧下卻成了兼顧市場與審美的顯學。美學階級隨著社會文化的觀點而不斷進行微調,甚至隨著時代遞嬗而產生微妙的位階變化,不過總的來說,愈是稀有而難以取得,愈能獲得青睞。機械化普及的時代,手藝特別難能可貴,然而在手工普遍的時代,不受人為控制、渾然天成的藝術效果更為高超,無論怎麼樣,人類總有一套辦法來論斷美的高低。
嚴格說起來,清輝窯的小吃碗並沒有做到機械化的完美複製,早年的移印技術並不精緻,造成各種青花釉印深淺不一、毛邊與出格的微小失準,說它「碗碗有瑕」也不為過,這正是清輝窯與後來接收清輝窯移印機器、異地重生的CK全國瓷器最大的差異—CK全國瓷器複製了清輝窯的圖騰,隨著科技提升,大幅改善了產品的良率,現今已經能達到高水準格式化的複製輸出,幾乎做到每一只碗的印花無論色澤與線條皆如出一轍的境界,這個境界在科技業無疑是一種讚譽,在美學世界裡卻造成了失落,精準圖樣看起來更乾淨俐落,卻因為失去了「意外」的野趣,顯得相對平板單調。
然而,即使早期清輝窯機械移印不斷顯露出肉眼可見的瑕疵,在藏家眼中依然不能與手工的不完美相提並論,這個偏見正好說明了文明進程裡出現的另一個詭異矛盾:手工生產的時代不免要走向機械化生產的道路,走上了機械化生產的道路後,人類卻在精神上開始緬懷人之所以為人(而不是機器),多少會「走閃」(tsau-siam)、會犯錯,能製造如台語所說那樣沒那麼「利」(lāi)、較「活」(ua'h)的自然拙趣,或因不完美而自然流露的人性。是以文化雅好者不約而同追捧無法高速量產的手工藝品,以維護一種不從眾的浪漫情懷,並從收藏這種人性產物的過程中試圖體驗不可言喻的人本精神與文明昇華,或彰顯不甘流俗的高度。
自從十九世紀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在《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Das Kunstwerk im Zeitalter seiner technischen Reproduzierbarkei)裡解說了「靈光」(aura)概念之後,複製品的靈光消逝似乎成了工業化時代裡無可奈何的詛咒,因此也不難想像,在許多人眼中,清輝窯的製作與藝術表達方式,礙於缺乏人性與靈魂的機械從中作梗,或許仍隸屬於「比較沒有靈光」的那個世界吧。
相較於文史學者與收藏家談起清輝窯時的茫然與情感匱乏,日用五金批發業者聽到清輝窯的反應相對親切而熟悉,小吃業者也許不知道自己使用的碗是清輝窯所產,但是他們對清輝窯早期小吃碗的形貌並不陌生。在傳統五金批發業者與小吃業者的眼中,食器的價值評量方式與文史藝術位階的價值界定方式顯然有巨大的歧異,甚至反其道而行─他們更樂於因襲常規與熱潮,什麼樣的東西受歡迎,他們就擁抱它。
出於這種「從眾」的心態,以台北後火車站的老字號五金行「金聲號」為例,它不但與清輝窯過從甚密,更曾因大量進口日本器皿,知道消費者喜歡哪一種日式花樣的食器,從而建議上游的窯場製作類似風格,使得台灣民器不僅在技術上,也在風格上都複製了日本模式。
我並無意透過清輝窯與小吃店家的故事去鋪展線性的歷史進程,也無意將清輝窯塑造為成功故事的典範(即使它確實成功踏上了自己所期待的新大陸),僅能倚靠一些來人的指路,勾勒出一張在台灣各地閃爍的歷史星圖。我認為,這些因為小吃碗而產生關連的小城故事裡,最迷人的地方在於他們一概在極度壓迫的時代、空間或經濟壓力之中,找到了一個足以獲得社會支持的出發點,生機勃勃地從種種逼仄的狹縫中出發,自此開枝散葉,長成了各種讓人感動的樣子。
套句詩人李歐納‧柯恩(Leonard Cohen)的話說:「萬物皆有裂罅,那是透光之處。」
(本文選自《小吃碗上外太空》,有鹿文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