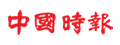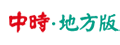指甲油

所有事物的末端,總特別虛弱──
後院母親栽的百香果,藤蔓長得豐盛可愛,青綠色迅速蔭遮一片,才經幾天烈曬,就從尾端開始,一葉葉枯黃、卷翹、乾透,隨風輕輕墜至泥地。人身也如樹藤,秋冬臨近,我手腳冰冷的時期又將來到,早晨在廚房,來訪的阿姨提醒搬上台北、獨居棲身的我,要記得多燉煮湯品,溫補潤身。「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子貢這段為商紂的校正平反,也令國中的我印象深刻。水流到了最底端,最冷最窮,人人可以落井下石,百惡居而善無存。惡居下流四字,記到如今。
人體唯一可以隨意捨棄、須要時時裁減的地方,也在頭、手、腳的盡處──頭髮長了就修、指甲長了就剪。可丟、可棄、可理所當然地不加珍視。它們明明由身上長出,卻彷彿是截然的身外之物。不痛,無感,可以盡情捨離。
然而就是這些可拋擲的枝微末節,最讓人上心。譬如指甲油。
某次塗了黑色指甲油,四歲姪子初次看到,剛開始會咿咿呀呀講話的他,突然安靜下來,偎到我的身邊,小貓似地嗚嗚輕哼,眼睛一直盯著我的指尖。
「姑姑妳怎麼了?」
「啊……這個嗎,」我皺起了臉,像小酸梅。「姑姑受傷了,好痛。」
常在屋裡邊尖叫邊橫衝直撞,腿上留下不少烏青經驗的他,立刻心領神會,用小胖手撫摸我的手指。手勁輕巧,有些怯生生地,怕弄疼了我。
小娃兒胖手溫軟的魅力,不能小看,絕對是一試成癮。下一回我新擦了艷紅指甲油,興沖沖地提起手,亮給姪子看──「你看姑姑怎麼了?」他停下玩積木,斜眼一瞄,沒有接話。「流血了嗚嗚。」力道不足,我再加碼。「真的嗎?」單眼皮眼睛裡,閃動懷疑的光。我兩手徒勞如蕉晾在空中,此時只能乖乖收回。
人果然是智人種,小兒一暝大一寸,腦袋也沒有白長。姑姑欣慰之餘,有點惆悵。
姪子的指甲油初次印象在四歲,我的指甲油啟蒙,在小學四年級。在沒有家樂福、全聯的時代,宜蘭賣場由喜互惠稱霸。記得那日媽媽帶我,走過一排排商品層架,突然間,我腳步停在一列架子前,硬是不走。
一顆顆小小的透明玻璃瓶,盛裝不同顏色,展櫃光線一照,晶潤潤地,像繽紛釉色的糖果。這是什麼,我問。擦在指甲上的指甲油。媽媽好笑地看我,順著我的意,在購物籃內放入一瓶正紅色的指甲油。
回到家,媽媽坐在梳妝台前,我坐在床緣,她扭開瓶蓋,為我小小的指甲一一塗擦。有機溶劑氣味很嗆,紅色很野,什麼東西像火一樣,搔著心。有一點侷促不安,但希望濃烈顏色繼續塗抹、覆蓋,不要停下。塗到腳趾的時候──右腳第二趾還是第三趾──父親打開門,撞見媽媽彎腰為我擦紅腳趾的一幕,三人視線驚愕交會,姿勢尷尬。他如風暴中止一切,責備母親,並把整瓶新指甲油俐落丟入了垃圾桶。小小的火苗瞬息被掐滅,早夭的心之躁動。
直接丟棄孩子的新玩具,而且不給任何理由,看似粗暴,但現在回想,此舉出自萬事保護的父親,其實毫不意外。如果可以,我也希望姪兒永遠不要長大,每天用小胖手暖暖地安慰我。
然而人為什麼會由自然界萃取豔彩色澤、塗擦於身呢?尚為小女孩的我,為什麼會站在櫃前,被晶亮的事物迷了魂?為什麼父親一看到正紅指甲油,會立刻將之視為禁物呢?如果顏色只是顏色,指甲只是外於己身之物,指甲油只是色料與溶劑的混合。
「禁忌賦予了它所禁之物自身的價值。......禁忌賦予意義給它所拒之物,而禁忌的行為本身並沒有這層意義。」巴塔耶說。可惜父親跟巴塔耶不熟,不然就會知道他已經油上添火,親自為指甲油的魅惑力,正式賦形。
將散沫花搗碎、將金銀粉撒入、將染劑注入樹膠蜂蠟,巴比倫勇士指甲染黑,克麗奧佩脫拉女王指尖血色,是時尚、階級還是情色墮落的象徵?代代的我們都傾心微小末處,喜愛炫目事物。
經過數年空白,大學時,才開始擦起指甲油。初時仍帶一點羞赧,客氣從透明、碎亮片著手,接續各種紅粉、暖橘、藕紫、可可、榛果,直至最飽和的黑和紅。各種色彩富有暗示意味,塗抹時心會竊喜、會搖擺,下重色時,需要一點勇氣狠意,像一場小小越界、限定的冒險。
我無法深入美甲系統,始終搞不懂鑲鑽與繁複圖樣,只是單色的信眾。在家裡轉開瓶蓋,為自己在燈下,塗擦一層,手指在空中晃一晃、也許讓身體跳跳舞,然後再上另一層。性情微躁,等不到底,每次半乾就這邊碰碰那邊弄弄,收拾什物,剛塗完的亮面,時常被磕碰上不少邊角壓痕。這樣細節的不完美,顯現性格,自己看著發笑,笑笑也就接受了──再怎麼說,指甲油也只是幾日的亮彩,總是得卸下的。
指甲油也不是日日擦,個性除了浮動,也懶。在意美,卻也不是那麼勤勞。在重要活動或約會前,才搭衣著配上。色彩選擇端看服裝和場合,有時霧面裸色,淡麗清朗;有時因服裝過於簡淨,揀個反差的跳色。
前任的美學品味偏向日系侘寂,對視覺感受頗為要求挑剔,這是他的強大優點。交往後,曾說他討厭擦艷色指甲的女子,但初次見面,看到擦著紅指甲油的我,竟覺得美,不顯招搖,一見便心內鍾情。這真是句上好情話。指甲油只是一層表象,它有暗示,卻不宜過度詮釋。它有指向,但更像一則邀請──你能不能穿透表象,從枝微末節,看見整體的我,理解其間轉折的意念。
畢竟油彩會卸,妝痕消融,樂趣之最,是上彩前那一時片刻、挑揀色澤的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