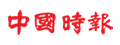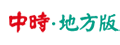浮生小記

說到「浮生」,不禁想起李白說過的話:「光陰者百代之過客也;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因為誠如莊子所云:人在世間,「其生若浮」,無根無蒂,飄飄蕩蕩。而處於無窮無盡的宇宙時空下,焉能不惆悵於如煙如夢之中。而所謂「小記」,卻用簡單的文字,要記載莫知所歸的「浮生」,使之留下痕跡。而我已為「浮生」三十年留下的「小記」,如今看來,竟覺得滋味無窮;可是仔細回顧其來龍去脈,我是從中國文學所呈現的生命境界,經過長遠時間,逐次體會而身體力行,然後獲得的。
我們讀陳子昂〈登幽州台歌〉,固然領略他遭時不偶,未能像樂毅與燕昭王那樣的君臣相得,而從中引發他一己的失落之感;但其間更濃烈的悵惘,則是他既不及見典型宿昔的古聖先賢,也未能見到可以繼述他志業的同道後人。他唯獨能感受存在的,不過是無邊的宇宙時空兩相交會的那一丁點那一霎那;而卻要以微不足道之身去面對承受那悠悠然籠罩下的無止盡天地,他怎能不孤寂而形神俱傷的涕泗橫流呢!
陳子昂的形神俱傷,可以說道盡了亙古以來人們「浮生」的共同無望和悲悽。於是有人想要突破這種幽微對浩瀚的無奈與悲涼,開始探索生命的真諦和歸趨:發現「服食求神仙」,以為可以使生命增加長度;但到底「多為藥所誤」,古今從未見有人因「九轉丹廻」而成仙了道。又有人認為立功立德立言,為「三不朽」可以標榜青史,傳諸後世;但畢竟「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使得許多人都看透人生在世,既如蜉蝣,又如朝露,「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來個朝歡暮樂,反而可以增添生命的密度。
我們且看看李白的生平志業。他原來也要像姜子牙那樣,不惜「廣張三千六百釣」,只希望有朝一日「風期暗與文王親。」可是他落空了,他學習了魏晉間人那樣談玄說理,以仙道要超脫塵寰,但那畢竟虛無,焉能如願?所以最後便落得杜甫對他最為婉惜的「痛飲狂歌」而「空度日」了。
李白一生身命的逐次陷落,可以說是古今讀書人一再反覆的模式和歷程。因為有抱負的讀書人,大抵都像辛棄疾那樣希企「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所以像曹植雖貴為藩王,但朝廷不給他報效的機會,他就認為自己「禽息鳥視」,「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那貌寢口訥的左思,以〈三都賦〉洛陽紙貴,還是要「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殷切期望於「鉛刀貴一割,夢想騁良圖。」然而「仁人願景長不遂,志士癡心可奈何?」這比比然的志士仁人,捨「痛飲狂歌」之外,還有其他如何自處之道呢?
我們發現了陶淵明由早年的「猛志逸四海」,到不堪五斗米折腰的「歸田園居」而「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而終於「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我們也看到了蘇東坡之廟堂得意,也看到他,「烏臺詩案」身命朝不保夕;更看到他三度謫遷,浪跡天涯。他體會了「事如春夢了無痕」,他「回首向來蕭瑟處,也無風雨也無晴。」他說「夢裡曾經遷海外,醉中不覺到江南。」他善於將現實遭遇的一切禍難痛苦,推向似有若無的夢境,使之不沾滯於胸中,成就了世人所仰望的「坡仙」。而我們也看到了王靜安先生,集古今學問於一身,融通中西涵養於一爐,卻倡道「人生過處惟存悔,知識增時只益疑。」而使自己承受不了無盡的悔恨和難於解釋的疑惑,而自沈於大明湖。
像以上這些文豪賢哲,他們所抱持的身命歸趨,都可以教我們省思。我認為靜安先生最不可效法,因為他「聰明反被聰明誤」,自作痛苦也自受痛苦。東坡縱使灑脫於醉夢之間,只是其「也無風雨也無晴」,不免有強作說辭否定事實之嫌。沈君山先生說他追求曾麗華,「也有風雨也有情」,儘管描摩了一幅浮世繪,但似乎不如說「一番風雨一番晴」,來得既勇於兩相面對周折,也樂於彼此品賞甘甜。我很欣然於淵明的物我兩忘,也欽慕他縱浪於大自然的變化流轉;然而如此修為,幾人能夠?
於是我在所從事的「中國文學」中,疏理其所呈現的生命境界,尋找可以使我安身立命的路途,終於體悟到「人間愉快」是其持之以恒的「不二法門」。對此,我不止著為專文,也輯為文集。大意是說:所謂「人間」,是指人世間,是你我他俯仰視息的地方;所謂「愉快」是指油油然汩汩然從胸中生發的舒服,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地。也因此,我們的「人世間」不必追求耶穌的天堂,也無須企慕佛菩薩的西方;我們的「愉快」,不假託名利來妝點,也不藉助權勢來助長。我們僅求諸耳目所感,你我他遇合之際;我們培養擔荷、化解、包容、觀賞的四種基本能力,現世種福田,現世享福果,達成相欣相賞、相激相勵、相顧相成,「蓮花步步生」的期許。
我相信這樣「人間愉快」的身命期許,那怕「浮生」瞬如水渦,飄似飛絮,也都會在你所屬的時空交會裡不虛此行。也因此,我對於東坡所感喟的「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知東西。」並不全然認同。試想:如此的「雪泥鴻爪」,「鴻爪」豈不已留在雪泥之上,又焉能隨鴻飛而消失?我們的「浮生」,既已為「小記」,何嘗不也如此?何況凡事經過,必留遺跡。這「遺跡」,在當時感受的滋味或許酸甜苦辣並陳,情緒或許喜怒哀樂兼具;然而一旦回首,重新檢點,也許尚不免「風也瀟瀟,雨也瀟瀟」的惆悵;而何嘗不更有「而今同踏相思路,白髮婆娑語未殊」的溫情?如此,倘能再將「距離美感」,濟以「人間愉快」的諸般體認,則「往日情懷」豈不又在「陳年故事」裡,煥發更亮麗的華彩?
也因此又使我想到,古代史官為什麼要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帝王要有起居注、實錄、本紀,列侯要有世家、名臣要有列傳?而士大夫傳記碑銘更見諸歷代典籍,遊記、日記,也充斥篇章。豈不都為了要使「浮生陳跡」,留存永恒。不止可以使千秋歷歷如繪,既能垂範來茲,也可借鑑前車。
我們都知道清人沈復的《浮生六記》,現存的〈閨房記樂〉、〈閒情記趣〉、〈坎坷記愁〉、〈浪跡記快〉,其內容不過記敘他們夫妻間平凡的家居生活和浪跡各地的見聞,以及碰到的坎坷遭遇,而其文筆則簡潔樸素,感情則真摯自然;從而將世態人情刻畫得栩栩如生,成為耐人品味喜讀的文學作品。於是沈復的「浮生」長存人們心目之中,也就不如煙如夢了。他自己不必建功以立名,也不必求仙以悟道,更不必痛飲狂歌以宣洩牢騷;他只將「浮生的遺跡」,用筆墨來敘寫,就可以使他一己之身命光華滿溢,使世人之身心充盈美感。
當今之世人有見及此,要為浮生留下遺跡的人越來越多,而且取道多方,就我所知的朋友而言,如許常惠以音樂、柯錫杰以鏡頭、郭清治以雕塑,薛平南以書法,劉桂鴻以彩繪、楊牧以新詩……,他們真是同明相照、琳瑯滿目。而我最鍾情於用筆用紙敘寫「浮生小記」。因為其隨身可及,最為簡便。我的「浮生小記」,無須像沈復那樣設題成篇,只是因時因地因人因物,所見所遇所聞所感,而乘興吟咏記敘,由於其以生活為內容,就宜於逐日為之,而成為所謂之「日記」。
我在五十歲以前,沒有寫「日記」的念頭,深知自己成不了大器,不過是個陽春教授、純正讀書人。平生所行所為只是讀書、教書,喝喝酒、寫寫文章;所來往的人,也僅是學生親友同仁;毫無可供世人稱述的地方。那麼還有什麼理由和動力,為自己的「浮生」留下「小記」呢?然而卻有一樣嵌入骨髓的「癖好」,喜歡於良辰美景之前,或登山涉水之際,或久別重逢之會;乃至於酒筵清歡、知交訴恨之時;每好口占舊詩五七律絕,融合眼前情景,即興而抒感寫懷。對於這些即興律絕,往往隨手分贈,或棄置不理。我當年於「塞北江南酒,飄洋過海詩」的萬里行旅中,不知撒漫「多少佳句」於人間。直到五十歲那年,在「酒党老弱殘登山隊」一次「郊遊」裡,沈毅口中吟哦有聲,原來是在朗誦我不知何時於杏花林即景所賦的兩首七絕,我覺得頗能寫照當時眼前興會;而李善馨也從他隨身的包包掏出一疊參差不齊的紙頭,一看,同樣是我們登山或聚會時,我遺棄而被他撿存的「口占律絕」。我從兩位老哥那裡又重溫了一起有過的「往日情景」,而且是那麼的歷歷在目。李哥說:不要隨寫隨丟,每個日子每件事的「陳跡」,都將會回味無窮。
從此,我聽從李哥的話,留下即興的五七律絕,又不時加上小注,「小注」發展為小記;後來「喧賓奪主」,有記而無詩,或詩記兼具。而我的「浮生」果然藉著小詩小記留下「痕跡」,迄今已充斥龐然。年來因病開刀在家休養,加上新冠疫情猖獗,困居斗室,形同禁閉,乃重新整理檢閱已裒然成冊的《舊詩小記稿》。其中所記及之人物時地、所見所感所思所懷,又鮮活的展現開來。時光為之而倒流,身命為之而回歸;而其間所流動的姿韻,則紛至沓來。至此我更體會到,「小記」並非等閒無聊之舉,而是使「浮生」眾彩並陳的泉源。在我這眾彩並陳的「浮生」中,也同沈復一般,看不到「豐功」、也見不到榮名勝事,更沒有「仙道遐思」,也不致於有「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的百般無奈。而與沈復不盡相同的是:盈編累牘的儘在講究「人間愉快」與「蓮花步步生」,而於山水煙嵐迷離之中,領略其如夢如幻的恍惚之美;也於「嚶嚶鳥鳴、求其友聲」,萬族有託之際,忘形忘我於物物相得;而這都斑斑點點的在《浮生小記》中逞耀揚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