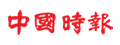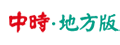黑夜的結束總伴隨著死亡的開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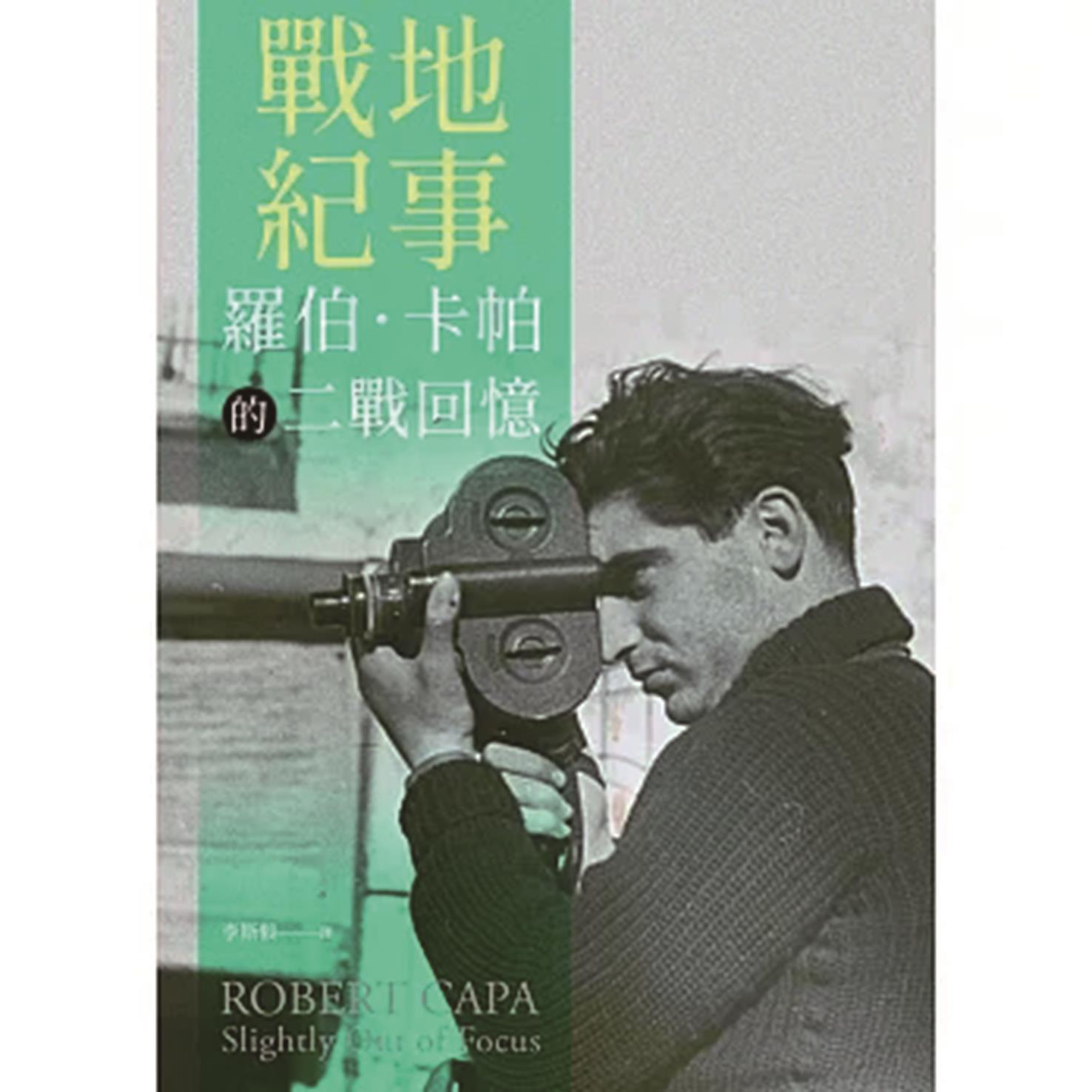
從北非到萊茵河畔,我已經經歷過太多次入侵行動,每一次我們都必須在半夜起床,黑夜的結束總伴隨著死亡的開端。可是這次的行動不同,我們在早上七點鐘各吃了雙份新鮮雞蛋,吃飽不久後才正式出發。
我和軍團司令一起搭乘領頭戰機,我會跟在他後面,成為第二個跳出飛機的人。登機前,軍團少校偷偷把我拉到一旁,告訴我如果軍團司令在看到跳傘信號之後踟躕不前,我得負責把他踢下飛機。少校的這番話讓我感覺自己非常重要,而且充滿欣慰。
我們的戰機在法國上空低空飛行,隔著敞開的機門,寧靜的法國景緻此刻從年輕士兵的眼前飛快掠過,沒有人因為緊張而嘔吐。這真的是一次非常不同的入侵行動。
數以千計的戰機和滑翔機同時從英國和法國的機場起飛,然後在比利時上空會合。會合之後,我們便以緊密的隊形一同飛行。戰機和滑翔機的影子從各個被解放國家的馬路及街道上方飛過,我們看見人們對著我們揮手,連狗也被我們迷住,追著我們的影子奔跑。我們兩側都有拖著滑翔機的戰機,宛如從英吉利海峽拖著紡紗一路來到萊茵河,每隔一百碼就又掛上許多玩具飛機。
我不想看太多或想太多,於是裝模作樣地開始閱讀一本推理小說。到了上午十點十五分,我只讀到第六十七頁,但是提醒我們準備跳傘的紅色信號燈亮了。當下我有一個愚蠢的想法,很想推辭地說:「不好意思,我沒辦法跳傘,因為我必須把這本小說讀完。」
我站了起來,確定照相機穩穩地綁在我的腿上,而且隨身酒壺放在我胸前的口袋裡,緊緊貼在我的心臟上方。距離我們跳傘還有十五分鐘,我開始思考我的過往人生,感覺就像觀賞一部電影,只不過投影機發瘋似地飛快運轉,我在十二分鐘內平淡地看見並感受我曾吃過和做過的一切。我感到非常空虛。最後只剩下三分鐘的時間。我站在上校身後看著敞開的機門,萊茵河在我們正下方六百英呎處。這時敵軍的子彈開始像鵝卵石般射擊我們的飛機,綠色信號燈亮了,我不必把上校踢出去,往外跳的年輕士兵們則紛紛大喊著:「該死的笨蛋!」我心中默數著一、二、三,然後感覺到可愛的降落傘在我的頭頂上方打開。我祖父留給我的手錶顯示我降落到地面只花四十秒的時間,可是感覺就像經過了好幾個小時,讓我有足夠的時間解開照相機的繫帶,拍攝幾張照片,並且在著陸之前思考六、七件不同的事。我抵達地面後仍不停地按下快門,每個人都平貼在地面上,沒有人想要站起來。第一次的恐懼已經結束,我們不願意讓第二次的恐懼開始。
十碼外有一整片高大的樹林,在我後面跳下飛機的人有幾個降落在樹上,此時無助地掛在離地面五十英呎高的地方。
德軍的機關槍開始朝著掛在樹上的人開槍,我忍不住用匈牙利語大聲咒罵,然後把頭埋進草地裡。一個趴在我旁邊的年輕士兵抬起頭來。
「現在向猶太神明祈禱也沒用了。」他喊道。「祂們現在幫不上忙。」
我翻身轉為仰躺的姿勢,看見我們正上方只有一架飛機,是克里斯搭乘的銀色「空中堡壘」。但是它突然扭動了一下,機翼激烈震動並且瞬間起火燃燒。那架冒著黑煙的「空中堡壘」開始往下掉,當時我心想:「克里斯背叛了我,但是他會成為一名英雄。」就在飛機消失於樹林後方之前,我看見七個小黑點──那七個小黑點開出了七朵綻放的花朵。幸好他們及時跳機,降落傘也順利打開。
到了上午十一點,我已經拍完兩卷底片,並且抽了一根香菸。十一點三十分,我從我的酒壺裡喝了第一口酒,我們的軍團已經順利攻佔萊茵河的另一側,並且從墜毀的滑翔機上取出槍砲,抵達我們應該佔領和守住的道路。我們失去了很多同袍,但是這一次的行動比薩萊諾、安濟奧或諾曼第都來得容易許多。曾經在那些戰役中佔上風的德軍原本可能在這個地方殺光我們,可是他們被打敗了。下午我們便與其他軍團會合,我關上了照相機,因為我已經拍到足夠的照片。我開始尋找克里斯。
傍晚時分,我開始朝著萊茵河前進,但是我們與搭平底船過河的軍隊中間仍然隔著敵軍。我在路上發現一面又大又完整的絲質降落傘,立刻鑽進去裡面睡覺。絲綢很溫暖,我夢見自己不斷地收到寫著「回去滑雪,回去滑雪」的電報,有時候署名是「粉紅妹」,有時候是《生活》雜誌。
我於早晨抵達萊茵河,河上有兩座浮橋,上千名士兵正帶著槍砲過河。他們都焦急地詢問傘兵的狀況,我誇誇其談,但是他們不介意。
我到了第一座機場,問那裡的人知不知道史考特少校的下落。「他被送進來的時候腳踝骨折了。」一名空軍中尉告訴我。「半小時前,他已經被送回倫敦。」
從萊茵河到奧得河,槍戰很快就變成了搶劫。美國士兵奮力前進,遇到的抵抗越來越少,並且撿到越來越多德國相機、德國手槍和德國少女。他們深入德國的心臟地帶,發現德國人是非常愛乾淨的民族。這裡的房屋和農舍維持得就像他們在美國家鄉的房屋及農舍,完全不像早期戰役中看到的那些。
戰爭還沒結束,可是人與人之間已經變得和善,只剩下那些曾經進過布亨瓦德集中營、貝爾森集中營和達浩集中營的人還沒有辦法與德國女孩親密互動。在混亂的尾聲中,這場戰爭即將結束,士兵們雖然仍繼續開槍射擊,可是在精神上早已開始收拾行囊準備回家。
從萊茵河到奧得河的這段路程中,我沒有拍下任何照片。集中營裡已經湧進許多攝影記者,發表太多這類恐怖照片只會削弱整體效果。在短短一天之內,大家都看見了集中營裡那些可憐人有什麼樣的遭遇,可是到了明天,很少人還會關心那些可憐人的未來。
鬱鬱寡歡的德國人現在突然變得友善,但也無法引起我拍照的興趣。我只想拍攝我第一個遇到的俄國人,然後結束我在這場戰爭的工作。
俄國人原本在柏林作戰,但是當美國人來到萊比錫這座門戶城市時,其他的俄國人也抵達了奧得河。我們在萊比錫附近又進行了一場苦戰,萊比錫雖然由希特勒的菁英突擊隊保衛著,但是他們和其他德國人一樣,當他們殺了夠多美國人也受夠了自己時,就會大喊一聲「大家都是同志!」
我當時跟著第五步兵師的一個營,來到一座通往市中心的橋。第一排士兵已經開始準備過橋,我們很擔心這座橋隨時會被德軍炸毀。橋旁邊有一棟看起來很高級的四層樓公寓,從公寓可以俯瞰整座橋。於是我爬到那棟公寓的四樓,為匍匐前進的步兵拍幾張照片,說不定這些照片將會是我在這場戰爭中拍攝的最後作品。五名重型武器連的美國士兵也在這棟中產階級公寓的四樓架設起一座機關槍,以便掩護過橋的同袍。由於從窗戶射擊相當困難,負責指揮的中士和他的一名下屬便把機關槍移動到沒有保護的露天陽臺上。我在門口看著他們,他們架好機關槍之後,中士就走回屋內,由年輕的下士扣扳機進行射擊。
在戰爭中開最後一槍的最後一名士兵,與開第一槍的第一名士兵其實沒有太大差別。如果我把這種照片傳回紐約,肯定沒有媒體願意發佈一個普通士兵用一座普通機關槍進行射擊的照片。然而那個年輕下士有一張乾淨、明亮且稚嫩的臉龐,他手中的機關槍正在殺死法西斯分子,於是我走到陽臺上,站在距離他大約兩碼遠的地方,拿起照相機對準他的臉。我按下快門,這是我幾個星期以來所拍的第一張照片──沒想到也是那個年輕人死前的最後一張照片。
年輕下士原本緊繃的身體突然無聲地放鬆,然後癱軟無力地倒進公寓裡。他的臉上除了兩眼之間多出一個小洞之外,並沒有任何變化。他倒在地板上的頭旁邊漸漸聚積出一灘鮮血,他的脈搏停止了跳動。
中士摸摸年輕下士的手腕,然後跨過他的身體抓起機關槍。不過他已經不必再進行掩護射擊了,因為我方的士兵已經抵達橋的另一頭。
我拍到了最後一個死去的士兵的照片。在這場戰爭的最後一天,有一些優秀的同袍不幸戰死,而那些活著的人很快就會忘記他們。(二之二;摘自允晨文化《戰地紀事》)更多精彩內容請免費下載《翻爆》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