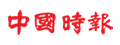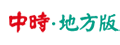氤氳時光

年幼時,每晚,慣與母親同寢。
我躺臥房內,淺橙綴花雙人床右側,一塊原屬父親眠睡之地。
我們共享的棉被底,擱淺的肉身上,藏匿近似的印。母親右腿近鼠蹊部,烙有蟬翼薄金色的痕,一只明顯漢字胎記,爽。我的右腿近鼠蹊部,則浮著一片縮小體積,橫躺,淡棕半透明的島嶼圖騰。
總殷殷期盼與母親共浴。
當她較早歇下自營古董店捲門,無需應酬,且家中少了陌生男子的深夜電話時,我們才一起共浴。母親總先行盥洗,半裸身子的我,赤腳,踟躕門外。三不五時,我叩叩門,輕問:「好了沒啊?好了沒啊?」有時耐不住性子,我踮起腳尖,轉開把手,讓氤氳水氣,從半敞的門縫,緩緩流出。「噯。再等等啊。」母親的聲音輕輕軟軟,沉析在看不見的水光底。我悄悄關門,半蹲,靜候母親允示。
乳白色系的浴室,鏡面滾著水珠,再疊上層層蒸氣,身處其中,便有失重般恍入雲霾之感。母親從浴缸中起身,無數細小河川,自她圓潤有致的身形滴淌。一座移動的瀑布,一尾毛孔迷散魅惑音符的魚,水漬迤邐,她邊哼曲,邊在洗手台前塗抹潔面霜。我急入澡缸,待潔身畢,將軟塞堵於缸口。我把蹲坐的小身體使勁朝龍頭出水方向擠,試圖將背後挪出空位,容納母親。
母親以白巾敷額,隨後,以雙掌緊貼浴缸兩側,再緩緩彎腰,屈身。最後她敞開白皙,飽滿的腿,讓我安然地把頭枕在她柔軟的肚腹。
飄蕩。晃移。久久。
在滿盈熱水的池裡,也有時,我轉身面對母親。我們笑鬧,指認彼此身上印記,眉宇間共有的痣,右腿胎記,母親乳房上的血色珠點,我左腕下的黑圓印,母親在看到我肚臍上的痣時,卻會嘆口氣。我問母親為何憂愁。
「這是過水痣呢。」她說,隨後不語。
沉默時,我們打開泡澡罐,讓水柱沖刷增生的瑩亮泡泡爬滿身軀。濃霧裡,母親半仰著,後腦抵牆而寐。我抓起澡缸邊的塑膠玩具,任其浮沉,同時在濃霧的迷障下,偷偷觀察母親。我喜歡她雙乳與腹部垂掛起一道道的微笑,喜歡她平坦的私處,喜歡她白玉羊脂般質地的肌。有時細沫褪去,顯現出她腿間林鬱,在波光蕩漾的折射效果下,像朵纖枝蠕動的海葵體。她的乳尖,溶洞景致般,垂著水滴。我看得出神。直到浴室裡,不再有足夠氧氣呼吸,且滴滴答答,下起從天花板凝結的雨,皮膚滾皺起老人皮,我才會不捨地搖醒她。
若無共浴,我也喜歡趁母親洗澡時,偷偷躲藏被窩裡。我雙手抱腳,緊縮身子,在逐漸濃密的二氧化碳與迷離的意識裡,等待。等母親疲憊地掀開被單時,驚呼:「你怎麼躲在這裡?」我喜歡她手足無措的表情。唯有介於沐浴後與睡前的母親,在溫水與蒸汽的浸染下,稍顯輕鬆。
母親在床頭櫃上,擺置分類而裝的各式錄音帶,漢聲小百科,中國童話,吳姐姐說歷史故事。每夜,母親要我坐在軟絨灰質地毯,聽半卷卡帶。她則獨坐梳妝台前,就著一盞光,筆記是日流水。直至卡帶磁卷軋盡,矮下的播放鈕,噠一聲,彈起,母親才停筆,走向我。靠坐身旁的她,擁我入懷,她要我每日上床前,完整背誦一首唐詩。我重複母親吟哦出,輕輕細細的賈島,李商隱,一字不漏重複母親的抑揚頓挫。當詞眼出了差池,母親用塑尺彈我掌心,當我朗讀得快速又準確時,母親則會愛憐地揉揉我的髮,將脣稍印於額際。
平躺於床,偶爾,母親要我再述那則童幼見聞,她名為阿賴耶識的回憶。我清晰能見,繾綣雲垛中,我身裹白錦,展一雙飽滿羽翼,飛上飛下,最後停滯於空,俯瞰,當時應是灰瓦矮房的國際學舍領地,已預先展演成一片綠茵,對街,簇新的合作金庫騎樓,許多男女行走其下,母親隱於人群。我左拐右繞,倚雲斜睨,最後一躍,墜入母親的肚腹底。
「為什麼選了我?」母親總反覆提問。
「因為我在天空中挑著,選著。這個太胖了,這個太醜了。最後,我選了妳。因為妳漂亮。」我理直氣壯地說。
母親曾提及妊娠七月時,她的鼠蹊處與大腿內側靜脈曲張,雙腳浮腫,行住坐臥皆難。同時父親因腦部動靜脈畸形進了手術房,疲於奔波,她只得於加護病房另添病床,每日平躺其上,注射綜合B群以緩下腹疼痛。「懷胎滿九月,醫護人員才敢鬆口祝賀,說總算成功地保住你了。」母親道。
夜深了。
我們熄燈。母親慣用日文道晚安。「休。」「休。」我們睡去。
當溫度與水氣散盡,月光跌入地平線,母親便在睡眠中,回復了嚴肅,僵硬的表情。若逢周末且無特殊活動時,於我,最是難熬。母親淺眠,平日有時應酬極晚,周末補眠,非要等到正午豔陽蹭過頭頂,她才起身。而我,總於天亮便醒,急著下床玩玩具。然而,我不能輕易動作,驚擾疲憊的母親。一個些微的翻身,或嘆息,母親即醒。
我睜眼,直瞅臥房天花板,床鋪正上位,那只圓形,積了塵埃的鐵絲雕花鏤空燈罩。我依牆上光影的移動,判定太陽相位,推算時間。我聽車聲。我用手指在棉被底下磨磨蹭蹭。就是不能翻身,或發出聲音。母親睡著。我看右側牆面上,掛著那幅缺了席的父親所遺下的作品。B4大小厚紙張,塗抹了四層色彩,由上至下,依序為純白、萎荷、豆沙與嫩磚色。在底層的豆沙與嫩磚間,父親黏上如音符攀爬的標本螃蟹數隻,與幾朵乾燥後的近海褐藻。
母親在旁,發出微微鼾鳴。我睜眼,在被窩裡想著許多問題,重溫許多畫面。
母親帶我去過幾次海灘,開著她的古董迷你奧斯汀,車裡總A面,B面反覆播放那捲蔡琴翻唱的錄音卡帶。魂縈舊夢,夜上海,恨不相逢未嫁時。我熟記周璇,白光,李香蘭的每句歌詞,我熟記每句歌詞,卻記不清是否父親曾經同行。我詢問母親,聆聽那些傷懷歌曲,是否懷念父親?她卻搖搖頭,回以一抹曖昧的笑。我記得下午的浪花嬉著腳丫子時,母親習慣站得遠些距離,風吹起她的短髮,她兀自凝望湛藍海面時的表情。母親不語。我手拿塑膠鏟,小圓紅桶,獨自在沙灘上挖尋各式珍寶。我將掏來的寄居蟹,沙馬仔與小貝殼盛於圓筒,再舀幾瓢海水。最後背對夕陽,我拉拉母親的短褲下擺,我們在飽滿愁思的懷舊歌聲中,返家。
若海岸屬於遠行,拜訪老爺爺,則為近程之旅。
有時,古董店打烊後的夜,母親載我探訪舊城區的算命老爺爺。
母親信其爻卦。妊娠一月,老爺爺能判男胎。待出生後批了時辰,便斷言我三歲無父。那年,術後的父親,確實赴美長期休養了。
算命室位公園邊。歸巢的車群,早歇了引擎躺於鐵蒺蔾欄外。母親常將迷你奧斯汀暫棲較遠的禁停車區,鄰近泰半是打烊的舊布莊,或霓虹醒目的神祕酒家。斑駁的磚紅日式樓房,拱廊相連,青苔蔓生,幾綹垂墜的慘綠纖草,在路燈下,格外陰森。母親不熄火,餘下冷氣,老歌,與我。
若於近處覓得車位,母親則帶我步入老爺爺的算命室。
民宅一樓的走道極暗,淺黃色的塑膠板,隔出一間間窄房。算命室居左,印象中,母親開門,暗影便迎面而至。老爺爺瘦伶,像條細黑而長的香草莢,被套進一件過大汗衫裡。他僂坐近木桌的凳。斜上是神龕,旁有胭紅神明燈,壇下,則是鋪滿油墨報紙與薄花被的木床。我畏懼老爺爺。他混濁,灰白的盲眼像窺伺著我的舉動。母親與之對坐,我總開溜到窗邊的等候椅。
母親以台語對談,所卜之事,多涉姻緣。或許因老爺爺曾提及母親命中太陽化忌,刑剋一生至親男性。我想起外公的早逝,二舅車禍身亡與父親的病。母親的起頭句,只詢問一段關係因何而終,何時而滅。得知對方生辰,老爺爺將兩枚油黑舊幣,塞入巴掌大的龜殼口尖。匡噹,匡噹,他雙掌執殼,上下輕甩數回,斜傾,讓銅板滾滑而落。他以指尖辨識陰陽,思忖半晌,後以古音述辭解句。
我極少參與對話,唯記一次,臨走前,母親要我同老爺爺道再見。我鼓起勇氣,問他什麼是過水痣。
「那意味你以後將離開這座島,並漂流至很遠,很遠的地方。」老爺爺以台語回覆。
「我捨不得離開母親。」憶及倆人右腿鼠蹊部篆寫的祕密,我說:「我們有同樣的胎記,注定相守一世。」
「常人道,胎記,備註了上輩子死亡的方式。」老爺爺用混濁,虛空的瞳孔對著我,說。
千萬不能動啊,不能吵醒母親,否則,便得覆轍那日光景。
床笫間不停翻身的我,令母親不耐。她起身,勒令我好好睡覺。「我很累,需要休息。」她說。母親背對,睡起回籠覺。我翻身,她起床勒令,如是重複。最後盛怒下,母親忽然掀開被褥,對我高聲咆哮,她要我收拾行李,滾出去。
我以為那是一句氣話,或玩笑。不是的,她狠狠瞪著我,不發一語。我在她冷峻的目光下,起床,動手收拾床右側矮櫃上堆的小玩具。母親起身,從櫥櫃內掏出一只小皮箱,丟在面前,我把懷裡捧著那些玩具,一個,一個慢慢放進皮箱裡。我哭了,刻意拉長,延緩動作,試圖挽救離家的命運。母親卻鐵著臉。催促著。
終究,闔上行李,母親幫我開門。我拎著小皮箱,一台階一台階走下,行李箱底與台階金屬邊碰撞出,喀噠,喀噠的聲音。我延緩步伐。然而母親聲聲催促著:「你給我滾出去。」
我流著淚,在四樓與三樓間的樓梯轉角處,停。窗外白花花的陽光灑在背脊,我卻奇冷無比,渾身打著哆嗦。我覺得我必須鎮定,仔細再看一眼母親,我要好好記住她,否則,便要像遺忘父親般記不清她的面容,她的身型。
身著睡衣的我,在四樓與三樓的樓梯轉角,仰望著。空氣凝結成冰,良久,她才開口說:「回來吧。」我破涕而笑,喀噠,喀噠,快步拎著皮箱上樓,躺回母親的床畔。
「不過你敢再打擾我睡覺,我就真的把你轟出去。」 背對我的母親說。這次我不敢動了,真的不敢動了,我閉上眼皮,仔細控制呼吸。我催眠自己,必須入睡,快點入睡。
在朦朧的意識裡,我半夢半醒,猶記一日,浴室裡,鬆軟的母親,我趴在她白色、濕粼的肚皮,我調皮問:「家裡有好幾間空房呢,為什麼我們要一起睡?」濃霧裡,母親的頭後仰著,聲音迷迷離離,沾滿水氣。
「有天,剛生你沒多久時,我抱著你,睡著了。你術後急性精神分裂的父親突然衝進臥室,掀開被單,逼我給他現金與車鑰匙。服用抗癲癇藥的他,是被禁止作用機械工具的。然而他逼我掏出鑰匙,否則,他說,他就拿刀殺了我們。」
「什麼時候的事?」
「正式離婚前幾年。」
「是這樣啊。」是這樣的。或許,有關父親的一切湮遠,源於刻意。
浴室裡的霧越來越厚。下起了滴滴答答的雨。快不能呼吸了。我暈暈睡去前,決定不叫醒母親。
我躺在母親的肚腹上,最後 對她說聲:「お休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