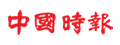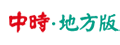唯心的地獄(下)─關於沙特劇作《沒有出口》
人間劇評
-203006.jpg)
至於愛絲特拉呢?
「我的父母早逝、弟弟又如許穉稚。無奈之中,只好嫁給一位大我三倍、和自己的父親一樣老的男人。兩年前我愛戀上一名青年,之後,便因肺炎而去世……難道這樣的犧牲也能算是『罪』嗎?──那些獄卒一定弄錯了!……」初時,如水晶一般青春瑩美的愛絲特拉對於自我的墜入地獄作了如斯的表述,為一己摩塑了一幅膠彩的聖女像。一個為愛犧牲的形像。
隨後,於伊內和卡辛的聯手「逼問」下,水晶形像瞬即碎裂:酷愛「探戈」與一切浮華虛榮的愛絲特拉愛上一位舞姿曼妙、卻一貧如洗的青年羅傑。愛絲特拉不慎懷孕,便佯稱「度假」潛往瑞士。在無人知曉的狀況下,祕密產下一女。陪伴的羅傑因而欣喜若狂,為這天使般的美麗降臨!
愛絲特拉卻為這突來的「意外」十分不悅。她將嬰兒帶至湖畔,找來大石……此時,羅傑正靠著陽台,俯瞰湖泊。「不!不!……」他失聲驚叫,不住求著她、求著她……直到湖面上僅餘一小圈磯波……於是,便折回房間,拿把槍,將臉轟個稀爛。
「其實,他大可不必!根本沒人知道。那老頭什麼也沒懷疑。」愛絲特拉聳聳眉評註道。
(除了卡辛,伊內與愛絲特拉在敘述的同時,也一再戀戀眺望那個「昔所戀棧,而今,已被註消、除名」的塵世──女同性戀者伊內發現昔所居住的房子已然租售,一對男女正在其間歡愛擁吻,因而狂憤妒恨不止。愛絲特拉則發現肥胖的密友正撫抱著自己的另一名情人,且將殺嬰的醜聞向他人公布出去。而卡辛,憤懣地聆聽著他胸中崇慕的高美茲對他所作的不堪評價──「懦夫!」,這正是卡辛最致命、最掙扎,亦最難以面對的。)
「地獄因」澄明顯示──然而,事情果真如卡辛所想像、以為的,溝通即是救贖之道?坦白惡質惡本、罪因罪行,即是和平、紓解之始?
誰能撫抱糞坑?舐愛蛆蟲?當沆臭的人性──如揭開的糞掃一般撲鼻而來?
這是慈悲者能,凡夫不能!
慧解者行,愚痴者不行!
大愛者是,利己者不成!
倘使所遇非人,告白罪行,僅是使傷口更益洞開、破漏,更形脆弱、惡化。如同摳指著一己最殘闕、致命的部位,拿著匕首致贈給敵人。
塵世已然逸出指尖,無論如何狂熱黏執,再也無能尋回、參與、扳回、補償些什麼了。伊內、卡辛,愛絲特拉都同時意識,他們所能擁抱、占有、支配的,僅有現實,僅是當下這個在地獄的男人,或女人。
女同性戀者伊內狂烈地意圖將愛絲特拉據為己有,如一隻火燎的鷲鷹般,全然無法放棄爪間的腐肉。縱任官能的愛絲特拉卻只想牢牢攫住獄中僅存的男性,滿足肉體的狂歡。而卡辛,作為一名曾經對自己有過一點理想、懷抱的智識人與和平者(即使僅是一點幻念)所追尋的,卻是精神的理解和補贖。單純的女體並不足以填補心魂巨大的虧空與失落,他需要的是基礎的忠實與信念(這是徒具軀殼、麻木殺嬰的愛絲特拉所無能賦予的)。卡辛無法返回陽世與他智性的對手作一決辯,斗室中,唯一吸引他、足具認同性的,僅是同樣知性、同樣犀利、而具穿視、洞澈力的伊內。
然伊內,卻憎恨這唯一的男性,妒恨他的存在奪佔了她可能的女性伴侶。
「懦夫!懦夫!懦夫!」相對於悲憫、同情或理解,伊內所能給予卡辛的,僅是更進一步的挑釁、譏諷與凌辱。
面對拒斥與反挫,卡辛的報復即是當著伊內擁吻、撫愛愛絲特拉……但是,狂越的激情畢竟無能持續……「多麼美妙的場景,懦夫卡辛抱著殺嬰者於他雄性的臂彎!……」於兩人的歡媾中,伊內不斷叫囂、嚎虐著,使得卡辛徹底癱瘓。
愛絲特拉拾起桌上的裁紙刀,衝向伊內,用力戳了又戳,戳了又戳……
伊內聳聳肩,揚聲大笑:「死了!死了!你明白嗎?我早已死了!刀子、毒藥、繩子……都沒有用……這就是永恒!」
永恒。
無間的地獄。
沒有死亡。沒有睡眠。缺乏休息,與紓解。不能去除自己,以及他人。
唯有靈魂對著靈魂。騷動對著騷動。
愛渴對著愛渴。灼迫對著灼迫……
還有,匕首對著匕首,殺戮對著殺戮,憎恨,嫉妒、凌辱、陰暗、蝕冷,酷毒……皆睜著腥羶的眼,兇肆對峙著。
無須任何刑具,僅三人,即足以形成錮拷、磨碾、永續無止的煉獄。
那麼,我們果真需要等至死後才直墜地獄嗎?或者,相反地,於死後才昇上蓮花皎澈、潔淨清芬的淨土?
抑或是,在每一日,每一時,每一刻的生活生息中,在實存的人際關係、經驗、情境,與對話中,人們早已不知不覺經驗過無數天堂與地獄、垢土與淨土的溯洄往返、上昇與下降?
而所謂的「地獄」,所指涉的亦僅是一種狀態:當我們與所厭憎、所不喜、或排斥的「東西」縛綁在一起──無論人、事、物……厭憎,而無能遠離;焦慮,而無以袚除;愛渴,卻無以抵達……即構成了「地獄」的情境與心境──比如,一個房間的顏色、裝置,一件家具,一支遍尋不得的牙刷,渴望鏡像卻尋不到一只鏡子,一件不對的衣裳和髮型,欲求溝通卻永遠曲扭的頻道……它們皆構成了某種「地獄」的質素與折磨……只是,有的稍縱即逝,一閃而過,幽隱微細地超越了凡夫心的意識與觀察,以致使我們無法覺知並認真思考它的存在。
作為一名極端智性的思考者,沙特所凝視到的,是「唯心的煉獄」實質居住、川流、蔓衍於我們生命生活的狀態,形成此世實存現實的一部份;一旦知見、好惡、情意傾向……衝突、齟齬,隨其扞格濃淡、強弱的不同,即自動形成大小不等的心間煉獄。同時,「唯心的煉獄」也平行指涉了「唯心的天堂」──人類的心靈、心像,決定了它所折射的角度。個體永遠具有「自由的意志」,去抉擇、改變、捏塑一己的存在與相貌。
如是,墮不墮地獄,居不居留於地獄,並不來自任何神祇的審判與責罰,僅取決於具體個人的思想,情感,性格、習氣,與行為……因為,我們堅牢的習氣與執取、嗜欲與偏執,(比如,人人的自私自用、愛憎對立,唯願隨逐、滿足自我,而無能理解、憐念他人)即構成了地獄最深植、頑固的存在。其中的輪轉,摧折與鞭韃正如伊內渴欲愛絲特拉,愛絲特拉糾纏卡辛,卡辛卻意願伊內……彼此追逐輪轉,如迴旋木馬一般,喧騰不已、傾軋不休。
然而,果真「沒有出口」嗎?
在臨去世前的第六年,六十八歲的智者/書寫者沙特陷入失明的黑域中。他孤獨、平和、清明地坐鎮於闃黑的牢獄中,平靜迎向他的死亡。因為,深知,保持自由,保持平定,不為束縛、奴役,與摧迫,即意味著牢獄的碎裂。
不是佛家,卻在漫長的精神走索與探詢之後,接近了修道者般的坦然與冥悟:意即,自覺,自在,與脫縛!
此間,放下執念,即接近了地獄的出口。(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