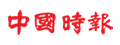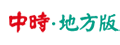蝜蝂
人間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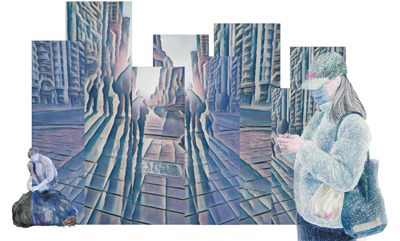
一個多年沒見的同學打Line給我,劈頭就說:「我的腿斷了。」
我愣了一下,回他:「我腿也斷過。你是怎麼斷的?」
「我最痛的不是腳,是我的眼睛。」
他沒頭沒尾講他自己的事,依然只想到自己。想起以前跟他相處的一些回憶,我頗為後悔接下了這通電話。我翻白眼,說:「骨釘拔完之後,醫生照我的X光,說我復原得很好,我現在偶爾還會慢跑。給你參考。」
他狐疑地說:「一點後遺症都沒有?」
我冷冷地說:「沒有吧。」
我掛掉他的電話,發現自己講得太多了。跟他講什麼骨釘、什麼慢跑?直接掛掉應該更好。
我站在一片雜亂的樂高、積木學習車跟兒童有聲書中,捏著自己的手機。腳拇指正巧在接電話的那瞬間,踩在一顆塑膠做的迷你貨車車頭燈上。
我聽見我的耳朵裡,穩定發作的高頻噪音。我右側的耳朵一直居住著安穩的耳鳴。
只有一切俱寂的時候,才聽得見那龐大的噪音。
小琛在嬰兒車裡熟睡。她穩定的吸氣、吐氣。秒針慢慢晃動的聲音。風聲從不綿密的窗縫中透進來,掀動水綠色的窗簾。我閉上眼深呼吸。嬰兒成長得很快。小琛根本不會記得誰在一片渾沌之中幫她把屎把尿,收拾一地的塑膠玩具。
今天夕陽很猛,擦窗的時候我感覺自己半邊臉都有點曬傷了。我聽見太太開門,她提早回來了。帶上門時,她淡淡地瞥了我一眼,把風衣脫下,掛在玄關的多功能壁掛。
「什麼事也沒有?」
「沒有。」
「Line這麼安靜,我以為出大事。」
「沒有,真的沒事。」我說:「我顧得很好。跟之前的每一天一樣。」
「今天一個大學同學打給我。」我說:「跟我說他出車禍,腿斷了。」
「要借錢喔?」
「沒有,只問我之前腿斷的事情,還講一些有的沒的。」
「你要小心。」太太露出很擔心的表情:「不要被騙。」
我實在懶得搭理她。拿起錢包準備去幫他們買晚餐,我說:「我今天沒煮。」
打開鞋櫃,想了一會,從中選出一雙很久沒穿的球鞋。太太忽然說:「明天你休息一天怎麼樣?我來顧。」
「這麼突然?」
「我明天放假。」
我想了一下,默默把大門打開,突然灌進一陣冷風刮得我滿臉刺痛。
「你愛去哪去哪。」太太多補了一句。
我腿第一次斷的時候,二十四歲。
我的骨釘剛放進去,因此在醫院休養多日。那時曾經許下一個宏願:「我絕不要活超過三十歲」。所以做了一件傻事:就是從高樓上跳了下來。如今想來我是無法接受自己一事無成三十年。那時為了追求一種誰也說不清楚的精神風格,咖啡與酒類能喝就喝。泡在日夜交際,神識昏亂的時間之中。我們讀了一些磚頭書,看些我們並不真的理解的理論、也追些當下流行的劇,整天連線打電腦、夜衝,反芻跟社會與人生相關的議題,發現並沒有任何解答以後,再全部拋到腦後。很專一地追求這種精神內耗,認為這就是生命的通透。
住在醫院的第三天,朋友們全來看我了,剛好能將我的病床圍起半圈。我對這些朋友開了一個不怎麼樣的玩笑:「我連去死都沒成功。」他們全笑了,我聽這些聲音忍不住也跟著笑。「這件事怎麼會傻到這種程度呢。所以之後我該怎麼辦?」我是這麼想。我們越笑越大聲,像房裡相互拍擊的浪。
那是我第一次發現人生的荒謬性。
第二次是看到兩條線的驗孕棒。
當時還不是太太的人有了孩子。我不知道該怎麼反應,懦弱、廢物、爛人.......許多負面詞彙一湧而上。這當然不在我的計劃之內,我自認自己完全做不了任何決定:無論是承擔或是不承擔都是。
一個月後,太太決定留下小琛。
「這是我自己的決定,你要不要負責?我不能強制決定,但我覺得你應該要。」她說得冷靜:「但我指的不是結婚,這不是這個狀況下最好的決定。」我腦中飛速運轉了一下,沒搞懂她的意思。她繼續說:「這個小孩不是沒你就會死。我的身體,我的人生,那都是我自己的事。我有自己的工作、存款。父母也自己都溝通好了。你欠不欠罵?是不是該死?我覺得是。但我不打算規定你要怎麼想。我有自己的社會經濟支持,我知道我擁有什麼。」太太瞇著眼,摸著咖啡杯的杯緣:「那你能提供什麼?......我跟你說這些,其實你要來說服我:為什麼需要和你走下去?」
我被她一連串的話堵得閉嘴。在沉默的思考中,我開始發現自己有無法甩脫的單側耳鳴。
安靜時它尤其巨大。忙碌起來雖可以忽視,但在休息時偶爾以暈眩的方式造訪。
醫生向我解釋這是梅尼爾氏症,我說:「這會好嗎?」醫生說:「或許你只能跟它共存,這問題不大啦!」醫生語調輕快,指揮在一旁觀診的實習生:「你幫這位先生清一下耳垢好嗎?」
「辛苦囉,辛苦囉──」
實習生連清個耳屎都能慰勞我,誠懇到我差點以為自己有付出了一些什麼。
我閉著眼讓天旋地轉慢慢止歇,默默希望這場廢退的旅程我可以到站下車。
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幹麼。我泡奶粉、換尿布,看著這顆小小的頭跟一對睜不開的眼睛,偶爾會對我嘔吐、大哭,有時像厲鬼令我害怕,有時卻會引動我的怒火,令我瞬間非常非常想殺人。
我喜歡這個小孩嗎?我常常問自己這個問題。每天被小琛搞到睡不好,吃不飽,還要擔心她發高燒、撞到頭、發育不夠正常、未來的開銷,這是愛嗎?
我想起我父親對我說:「丟臉哦你,還要人家來養你。」是否愛自己的小孩這一題,我想他是很有心得。我回他:「你也養媽媽啊,難道你覺得媽媽在家養小孩很丟臉喔?」
我沒得到什麼,除了一個疼痛的耳刮子。
我自找的。
我放假了,但還想沒好要去哪裏。我走到離家裡最近的一個捷運站,不進站,沿著捷運軌道的路線漫步。讓自己放空,感覺雙手的空無一物。
一路走來,經過了許多公休的店,我看到遠處有人潮,於是沒頭沒腦地跟了過去。
結果走到了那間準備收起來的,知名的二十四小時書店。我想起從前的太太很愛來這裡。她翻東翻西的,而我只是隨便走來走去。我很久沒看書了,還是很喜歡書店提供的某種氣氛:那讓我會逐漸感到安心,而且錯覺這是可以長久下去的事物。
荒謬的是,幾個月後這間店就要永遠熄燈了。上次來這裡,好像已是跟太太登記以前了?或更久?她總是第一時間先去看文學創作類的新書,再來就是商業財經類,最後就是心理勵志。我遵循著她以前的順序,也先去看了整排的文學類新書。這些冒出頭的新人我是一個也不認識了。那些我曾熟悉過的人名,和那群曾來醫院關心我斷腿的朋友一樣,已隨著時間流動到我肉眼不可見之處。
我想起那通電話──那位說自己最近腿也斷掉的同學。他亦曾經在我面前拿起一本書,開心地跟我分享他找這本很久了。真開心啊那時候,單單為了一本書就可以如此。
一位看起來國中生歲數的女孩子忽然從我面前的櫃子中抽走一本張愛玲的書。《半生緣》。我不知道現在有多少人會主動讀這本書,也不知道這在她的生命裡會產生多少意義?女孩子飛也似地挾那本書去結帳,離開書店。我腦海裡驀地響起那本書最經典的台詞:「我們回不去了。」張愛玲說得對。不管是誰,我們都已經永遠不能,也無法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