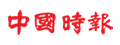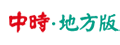她走過的年代
人間紀念

4月3日是母親99歲生日,算農曆的話,是百歲大壽了;於是子孫和曾孫三代人分別從美國、香港、多倫多訂了機票來給她賀壽。
沒想到,才差五天,她便走了。幸好,走得一點痛苦都沒有,雖然有點遺憾,倒沒讓人難過;活到這把年紀,中國人說是「笑喪」了,真可帶笑而去的。
過去好幾年,母親在老人院「華宮」裏生活得挺快樂的:一個人住在一個頗寬敞,又光線充足的大房間裡,老人家說話常重複,每次見她,她幾乎都以「三得」為傲;所謂「三得」就是「吃得、睡得、痾(大小便)得」。
除了心臟有潛在問題,她什麼小毛病都沒有,更難得的是心理健康──她從不埋怨任何人,對生活異常滿足;除了住溫哥華的二哥經常探望她,我和大哥、妹妹每年都從不同的地方飛來看她。近百高齡,四代同堂,她理應感到幸福。
可是好些人儘管有著她的處境,卻未必有著同樣心境,因為以她的生命歷程來說,她絕對有許多「怨」的理由。
她所經歷的艱辛,殊非這世代的人能想像。
她生長在廣東中山,父親是個小文員,母親看顧四個兒女,沒工作;抗戰槍聲響起,祖父連那分小差事都丟了,大舅舅遊手好閒,二舅和姨姨尚年幼,一家的生活重擔便落在母親肩上;那時她該才14、5歲吧,每天挑三十來斤雜貨(像用作燃料的「火水」)從小鎮石岐挑到農村翠微去賣,然後在翠微住一晚,翌日又挑同等重量的貨物(像稻米)回到小鎮賣;跟著休息一天,第四天重啟行程……。
這是無比艱辛的工作──石岐和翠微相距四十多公里,每天凌晨三時,母親和十來個同樣做買賣的人一起出發,為了避開盜賊,更要繞開大路,挑崎嶇的山路而行──肩膀上還挑了三十多斤貨啊!這樣一程,起碼須走八小時以上;有時,貨物未必能在翠微賣掉,這樣,她更要多走兩小時路,把剩餘的貨挑到澳門賣。
母親晚年體格那麼好,大抵跟她年輕時這樣的「鍛練」分不開的。
小小年紀,一根擔挑養活一家六口人,母親遂得到「三級石(她住那小區)奇女子」的稱號,這是讓她驕傲了一輩子的事。
抗戰結束,她過上了約十年好日子──她和父親結婚了,父親還在石岐最興旺的孫文西路開了間百貨店──中山人是中國百貨業的先驅,上海的永安、先施都是中山人開的;他們很自然的進入了這行業。婚後,她接連生下了我們四兄妹。母親除了持家,也「文君當爐」,站在櫃台裡賣貨──她長相漂亮,又好妝扮,為公司招來不少顧客,又因此得了「百貨皇后」之稱。
解放後,沒幾年,我家的「廣東百貨公司」就給「公私合營」了,再沒多久,更歸公所有;父母由老闆變成售貨員。
五七年,父親因為批評行內「外行領導內行」,被打成右派,幸好他趁工作單位不察覺,以照顧在香港的祖母為由,得街坊派出所批准,去了澳門。待工作單位知道,趕緊到海關攔截,幸而父親已過關,不然,我們一家的命運都要改寫。
可是從此開始,母親守了二十多年生寡──赴港後,父親不敢回到中山去,祇是每年一次,有如鵲橋相會,他冒險到廣州和母親相見。
1959年,二哥也獲批赴港;不久,母親下放到農村去了,主要是修建長江水庫;家裏祇剩下我和大哥、妹妹三人,那年大哥才十五歲,便當起家來。
我生性頑皮反叛,很抗拒學校教育,經常逃學;一次,母親從鄉下回來,押著我到學校去;眼看我走進課室,她放心的回家收拾行李下鄉;哪知她甫轉身,我瞬即翻牆而出,比她更早回到吾家附近;我躲在一柱子後,看到她提了行李離家,瞬間,我的眼淚不可抑止的流下來。
母親不住的向所屬街道派出所申請到香港和父親團聚,但都沒結果;卒之到了1962年,一個姓關的公安跟母親說:「讓你們所有人到香港是不可能了,要嘛你先走,把三個兒女留下來;要嘛我讓他們走,你留下來。」母親毫不猶豫的作出決定,自己留下來。
母親獨自在家鄉生活了約二十年,她不斷的申請去香港,都不獲批准,理由也說不清楚;一說,是對「右派」父親「逃港」對她的懲罰;另一說是,那時中國頗貧窮,亟須外匯,留一個人在國內,家人在港給她寄錢,多少可幫補外匯之不足。
她好幾次嘗試偷渡去澳門,但都失敗了,幸而懲罰不重,每次都關十來天就把她放出來。
直到文革結束,八十年代初期,她才獲批來港。她經深圳來港,我去深圳接她;那時港深之間的通道是架不大不小的羅湖橋,帶她過橋時,我跟她說:「你多笨,這條橋一分鐘就走完了,你卻走了二十年。」
據她說,結婚以來,從沒跟父親吵過架;可是待她來港,父親已經有了第二個女人。母親祇好到加拿大跟我的兩個哥哥生活,和父親離了婚。她早已習慣了一人獨自生活,所以離婚於她而言,或許無奈多於感情創傷。
算起來,她在加拿大生活了四十多年,日子無風無浪,異常的寧靜,尤其最後她待在老人院那八年,生活起居都有人照拂,她活得很安樂,跟前半生對比太大了。回想她的一生,我想起王安石的詩:「願為長安輕薄兒,生當開元天寶時。美酒輕裘過一生,天地興亡兩不知。」她後半生的日子過得很輕淡、卻很難得、很可貴。
她即將入土為安了,我總感覺,有必要把她的生平寫下來,才對得起她所經歷的時代;也讓後代認識一下,那曾存在過、他們沒法想像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