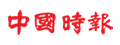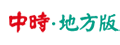聾嫂
人間如晴

早期剛回台灣時,我們一家住台大的舟山路。中文系方瑜教授家的小女兒和我家老二同班,我們又是同一社區。方教授介紹她家的清潔工給我,她就是聾嫂。
這兒的宿舍格局都一樣,起初聾嫂到我家時,總是沒好臉色,咿咿啊啊的叫著,沒人聽懂她要說什麼。我只能用猜的,也許小孩的玩具亂丟,也許茶几上未寫完的功課亂扔,讓她不高興。她一邊收拾,一邊把桌椅拖得乒乓響,好像我們都犯了錯。有時忍無可忍跟她說:「太大聲了,輕點!」說了也是白說,她壓根兒聽不到。也因為聽不到,對她而言,粗魯的動作似乎就更合理了。
雖然她粗枝大葉,但是家裡兩個重要的地方,倒是打掃得特別乾淨,一處是廚房一處是廁所。其他的地方,不順眼自己動手就是。
我家離社區大門間隔兩棟樓遠,但只要她來到宿舍大門口,就聽得見她和警衛打招呼時,彼此你來我往,有如爭吵般的問候。奇特的是多年下來,警衛竟也聽懂幾分她的咿啊。有次,我生病躺在床上,她看我滴水未進,就到廚房自顧在冰箱中一陣翻找,給我煮了碗雞肉粥。看到那碗粥,委實讓我驚訝,想不到她粗枝大葉的背後,也有細膩的一面。
不久,我把她介紹給來台講學的德國教授家。好在女主人是台灣人,對聾嫂的比手畫腳尚能領略幾分。一天,警察上門找我去德國教授家,說女主人丟了金飾,懷疑是聾嫂偷的。聾嫂一見我,彷彿看到親人,一股腦的咿咿哇哇不停,恁誰也不清楚她在說什麼。只見她比手畫腳,整張臉脹得通紅。我跟警察保證,聾嫂在我家從未拿過任何東西,是否誤會一場,請教授太太再找一找。就這樣,像場鬧劇的散了。
兩周後,教授太太來電,語帶歉意的說金飾找到了,要我趕緊請聾嫂回來工作。我告訴她,聾嫂已兩周沒來上工。
第三周,實在不放心,到大門警衛處,打聽到聾嫂家的地址。由舟山路走到基隆路,不遠就來到長興街的一處低矮民房。簡陋的平房油漆落盡,露出東一塊西一塊的水泥,猶如癩痢頭上的斑塊。屋前散落的一捆捆垃圾回收物,有紙箱有寶特瓶。
門是開著的,探頭入內叫喚,正在做飯的聾嫂見到我,先是一愣接著一連串嚷嚷,還在猜測她的意思時,忽聽牆角傳來一陣男聲:「請問妳有什麼事?」屋內幽暗,仔細看才發現一年輕男子坐在角落,眼窩塌陷微露眼白,一看就知是視障人士。說明來意和關心後,年輕男子慍怒:「我媽說有人誣賴她偷東西,不去打掃了,她寧可去撿垃圾!」
回程路上,心中升起一股歉疚感,來自對聾嫂一切的毫無所知。經打聽,才知聾嫂從小耳聾,嫁的也是耳聾的丈夫。兒子出生後不久,丈夫就車禍過世,留下這對耳聾的母親與眼盲的兒子。現在,母親是兒子生活的支柱,兒子是母親工作的動力。
敘述的人說罷,深深的嘆了口氣。那嘆氣像是從長長的故事裡滲出來的。
幾天後意外的,聾嫂來上工了。當客廳桌椅再度發出碰碰響時,我非但不覺煩躁,反而升起一絲的心安。工作完畢,聾嫂從自家帶來的塑膠袋中,掏出幾株紅鳳菜,就直接插在陽台上荒蕪的土缽裡。一周後,紅鳳菜冒出新芽,好似聾嫂種下的一盆心意!
我在舟山路住了四年,期間除了金飾誣賴事件,聾嫂總是準點出現。她的咿咿哇哇聲,像這宿舍的報時鐘。她也是這社區最出名的人物,雖然她的雇主只有四家,但所有的住戶都認識她。她一年四季戴著一頂草帽,穿著過膝的短褲。唯一不同的,僅在冬天加上件防風夾克。那頂草帽的邊兒都起毛了,褲子下靜脈曲張的兩條小腿,就插在黑色的半筒塑膠雨鞋裡。來時一陣腳踏車的鈴聲,去時一陣腳踏車的呼嘯。
搬離舟山路的那天,她意外出現。我以為她找到新雇主,要來工作。沒想到整個上午,她只是來幫忙搬家。臨走前將一疊鈔票放在她手中,向她道謝與道別。她不但拒收,還急得哇哇叫,怪的是這次我竟然聽懂她的意思,她希望我好好的過日子。
但怎樣才算是好好過日子?我想到她的日子,也想到自己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