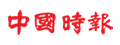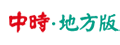風知道
人間小品

那年初夏,南風拂面,帶來微醺的恍惚,彷彿一杯溫過的白酒,將心事悄然攪動,令脈搏輕顫,神思飄忽如煙。
月台上人潮如墨滴墜入靜水,瞬間四散無蹤。唯有她,獨自佇立於第七車廂前。潔白襯衫隨風輕揚,與率性的牛仔褲交織成一種近乎矛盾的和諧,勾勒出纖細而堅韌的身影。一頭長髮鬆散披落,如夜空中碎裂的星光,眼神裡藏著尋覓與迷離,像是在等一班從未預定的列車。
列車啟動,她竟然坐在我身旁。
「我是畫童話的插畫家。」她的聲音輕柔,帶著自信的語調。「家裡有隻貓,最愛跳上畫桌,把本該完整的畫稿,踩成一張張意外的足跡地圖。」
她說話的語氣,像午後陽光灑落書頁,溫柔中帶著一絲甜糯,令人不自覺地安靜下來,只想聽她再多說一點,哪怕只是窗外的雲影。
退伍後的我,在書店搬書,夜裡埋首寫作,幻想文字終能開花結果。然而現實多半是沉默的,稿件如石沉大海,連回音都吝於給我。偶有回信,也只是冷淡的「謝謝,不適用。」
她愛翻我的筆記本,經常笑著唸出那些自以為浪漫的句子:
「如果風知道,就請輕輕地,替我抱住妳。」
她撇嘴:「你這句寫過幾百次了吧?風真的知道嗎?我不信,別騙人了!」
我說:「那些沒說出口的心事,風會知道。」
她笑了,笑聲如風掠過耳際,輕盈得讓人忍不住想捉住再聽一遍。
夕陽落在她臉上,那一刻,像幅未署名的畫,美得令人不敢眨眼。
我們常約在巷口那家咖啡館,對坐窗邊,沉默地望著公園裡那尊孤單的雕像。彷彿在彼此眼中,看見同樣的寂寥。
她用畫筆記下我埋首寫作時緊皺的眉頭;而我,則悄悄把她寫進小說裡,讓她成為唯一的主角,住在我無法言說的渴望裡。
她說:「就這樣聚聚,喝杯咖啡就很好。關於愛啊、承諾啊,都別提。那些話像石頭,丟進湖裡,會起漣漪,擾亂了心,回不去原本的平靜。」
她守著心裡那扇門,偶爾開個玩笑,卻很少真正打開它。
我那時年少,不懂,也不曾有耐心去觸碰他人過往的傷痕;她亦未曾試圖了解我的困境。我們像兩片在風中飄零的葉子,輕輕碰觸,卻無法停留。
直到那晚,我們散步經過公園。她忽然停下,凝視池水,緩緩道:
「有時候,我覺得自己像攀在懸崖邊的藤蔓。不敢往下看,也不知道還能撐多久。」
她沒有哭,只是悄然握住我的手。那一刻,我才明白,她的內心或許正經歷著一場無聲的風暴,而我卻天真地以為,時間終會治癒一切。
某日,她提及想辦一場畫展,在醫院長廊,名為《無人去過的城市》。那些畫作,皆是灰調,人物總在等待──窗邊、轉角、電梯門前……其實,畫裡的身影,皆是她心中不同面向的自己。
她的敏感與孤寂,讓我想起梵谷。那個在孤獨中燃燒、在靜默中瘋狂的畫家。她像他的靈魂翻版,不求被理解,只在畫布邊緣,封印破碎的自己。
我也附和告訴她,我想寫一本書,由妳畫封面,就叫《如果風知道》。
她望著我,似有話湧至脣邊,終究沉入無聲的深海。
然後,她就這樣,從我的生活裡消失了。
那晚風格外涼,我在咖啡館等到打烊,對面那張椅子空著,不知何時會來?
兩天後,她妹妹打來電話,聲音顫抖:「姐在加護病房。」
原來,她自大學起便與精神疾病共生。她害怕被憐憫,更怕拖累別人。她渴望愛,卻懼怕愛的重量會將彼此壓垮。於是,她選擇逃,選擇畫,把所有難以言說的情緒,細細藏進色彩裡,把易碎的靈魂,一筆一筆塗在畫紙邊角。
我翻著她留下的畫冊,一頁一頁──咖啡館、雕像前、書店巷口、夜裡依偎的長椅,還有第七車月台,我們相遇的起點。
畫中人影模糊如水中倒影,卻真實得刺痛。每一筆,都是她無聲的呼喊。
畫冊最後一頁,是她的背影。她坐在風中,長髮四散飛舞……
畫旁,是我曾寫下的那句笨拙情話:
「如果風知道,就請輕輕地,替我抱住妳。」
那一刻,我終於明白,我應是她願意停留的一處風景。
只可惜,我那時太年輕,聽不懂她溫柔語氣裡的暗示,沒給她足夠的溫暖。